我們面對的不過是死亡。天悅與天說一同長老。
臉孔與眼睛,天悅與天說,她看着她,在一間酒店房間摸索,她沒有盲掉,但如同在生命的最後日子,她沒有尋得,她沒有說。
天悅寫給天說的信。她問,你還有我寫給你的信,可否給我。天說從來不丟掉,不像天悅。
一個戀慕,一個忘懷,同一靈魂的兩種傷害。
「姊姊:你離我那麼遠,我想我可以將你忘記。」
天悅大吃一驚,年輕時候的信,她以為寫給情人。
每一個曾經在世上生存的人都是她的情人。原來我曾經那麼熱烈的愛。
天說給天悅買了一頂帽子,天悅記起,你上一次給我買的那一頂草帽,在愛丁堡,一個小島,不停下雨,她的帽子給濕過頂透。天悅戴着一頂微濕的帽子,她沒有除掉。
生命可以浪費嗎?如果當初我想像得珍貴。天悅從不珍惜,身外之物。此身也不。
天說在一張破沙發睡着。小臉微皺。當初她們的母親,可否分辨,一嬰與另一,天悅給天說一張她老了的影像,她說,是誰?是我嗎?我也覺得我是你。天悅掩面,天說低語:對不起。
只有在天悅的呼吸與微語之中,天說沉睡。我覺得我一生都沒有睡過,眼睜睜。
眼看着破壞與沉睡。愛丁堡真是寒冷,八月天氣,還要穿小皮夾克。
我們流放。但從來沒有人驅逐我們,沒有一個獨裁政府指令,這不是你的家。
我情願有一個獨裁政府,起碼恨得熱烈些,言語勇猛些,並且享受對抗。
我們面對的不過是死亡。上一次見面,天說要叫假香檳,一次在西班牙,天悅騙她姊,cava 就是香檳,這裏叫做cava。後來給天說識穿,cava 是假香檳。一群人說這說那,巴黎人很粗魯,推推撞撞,他們說,他們不是巴黎人。天悅開始頭痛,這一晚餐,頭痛的開始,她沒有搞清楚,是不是因為巴黎。
你那麼討厭巴黎,你總是跑回去。誰的話,天悅聽,笑了笑,你說的是。
上一次我們見面,天說解釋,在一個家族的婚禮,我很少見我妹妹。
婚禮關於愛?在那一個婚禮,有人說 agape,天悅寫下。她不能的時候,寫下,好像寫下就是完成;而她又很清楚的知道,並不。清楚至她的生活,與她的字,離離跌跌,生活剝盡,有暗有光。天悅的靈魂有影。
愛有所能?有所缺?巴黎的初冬,湯馬說,這一天來了冬。
塞納河夜奔無聲。他們走過聖母院。愛美莉說,我從來沒有見過無人的聖母院。
天悅一停步,天說耳朵卡嚓響動,「我聾了。我的耳朵愈來愈不清楚。我的右耳。」
其實我們都不需要耳朵。我們只需要聲音,沒有內容。
上一次,那一個下大雨的婚禮,天悅獨自行走。上一次,一個下大雨的早上,一個流浪人前來嚇她,手中有一隻濕透的血污鴿子。天說跑得遠遠的,讓天悅獨自對着流浪人。天悅打開傘子,給流浪漢擋雨。流浪漢離開。
他沒有要做什麼,街上人很多,天說走回來。
愛有所能,有所缺?
「在天亮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我亦會同樣出賣你。
「我沒有再到廣場去。」「每一個晚上,我完了工作,我都會去佔領區,晃一晃。他們都在,我不去不好。」「我很累很累,我想離開。」「只是覺得,如果我不走出來,就不會再有機會。」「一生一次。」「如果清場的話,我第一個會離開。」
廣場?佔領區?你開始悼念你的青春嗎?信仰?
從和諧廣場走到巴士底。「我沒有再到廣場去。」天悅到 Rue Soufflot買美術用品。也在這一條街,小革命者於一八四八年設置路障,並與國民軍衝突。之前的革命事件,給改編成音樂劇拍成電影,革命娛樂,很好看。
盧森堡公園的落葉還沒有盡,如果你夜歸,我怎樣走你的路,天說很會,溫柔的需索,即是說,你送我回去,無論這一個晚上,你的小腳趾如何呼喚痛。天悅沒叫她閉嘴,她是妹妹,她只說,這樣你跟我走,不要煩。她和她走到酒店房間去,她所記得,她們從來沒有在一個家生活過。
母親死後,留下的是天悅而不是天說,這是天悅永不可贖回的罪行,但她什麼都沒有做;父親決定,年幼的兩個只能留個。他不覺得殘忍,天悅也不覺得,人生下來就要接受審判,天說是個難帶的孩子,那個年代,僅僅有吃的年代,說愛太奢侈。
天悅記得,父親買了新衣服,綠色大衣,她以為是買給她的衣服,去修女院探天說,天說穿著一件藍色絨校褸,站在鐵絲網面前等他們,一見到,天說立刻跑回修女院房子裏面去。
他們沒有見着天說,父親留下了那一件綠色大衣。
我們的顏色,冬日之綠,天說將手放在大衣裏面。
姊妹都穿一件綠色大衣,不知什麼時候,在世界的兩處,隔了海洋與大洲,我們呼喚。
我們到 Monoprix 去,天悅喜盈盈的,她最喜歡的百貨公司,可以買洋菊蜜糖洗髮水,洗着有昨夜的睡香。天說要去買一對襪褲,小店裏的太貴,她又冷,蜜糖又太甜,沒有一件歡喜的事情,我在修女院長大,天悅雛眉,襪褲賣十二歐元九角而不是十三歐元,都是修女院的錯。
天說的反叛是,她是所有修女院的相反,天悅的幻滅與破裂,從一個咖啡杯開始,微小痕迹,直至國土分離。
完整不過是一個概念,小島飄流。每一個人都問,雨傘怎樣了?還好嗎?好像雨傘是她的舊情人,或許是。天說只專注,咖啡不夠熱,啤酒不夠冷,你肯定你想穿襪褲?天悅問她,那一年我在羅馬中央圖書館,熱得我脫掉襪褲,歐洲天氣,不像北美洲,到室內你會大腿發癢,天說堅持,我一定要買一雙襪褲,我到底穿也不穿。
姊妹是,無論你多麼厭惡與希望離開。你總回來,你甚至找到你的鄰居區域,第五區,Pantheon 在維修,白色帳蓬包圍的圓頂,天悅到莫芙達街街巿去買麵包,乳酪,愛美莉住在鄰街,打開窗,見到鄰屋的窗子,如果聖靈是鴿子,聖靈貪吃又到處屙屎,鴿屎綠白。
天說脫掉她的襪褲,很癢。她的完美世界,與修女院相反的,在一個巨大無比的行李箱裏面。那一年在馬德里,為了一個巨大無比的行李箱,姊妹吵架,你這麼重的行李,不是叫我做挑夫嗎,天說那麼嬌滴滴又無助的站着,如果你無法提起推動這麼一個家俬那麼大的行李箱,你為什麼堅持,行李箱裏面的,完美細節,生活的謊言,電爐,我只用我習慣用的水杯,杯墊,在北美洲的家,我只用四層的廁紙,如果豌豆公主可以感覺七層牀墊以下的沙粒小豆,天說一定可以感覺十四層牀墊以下的微塵。
或者,完美的不可能。她知道,她拒絕,這是她對世界的報復。
你拒絕相信,就不存在?革命是,受苦而又沉悶的人的娛樂?
那一個不存在的完美社會,你永遠期待。
天說沒有再收到信。群眾在廣場觀看斷頭的完美藝術,他們殺了路易十六,在和諧廣場。或者,有沒有倒吊的墨索里尼那麼好看,真可惜,他們殺壽西斯古及其妻的時候,不過是電視轉播,殺候賽因,沒趣味,那段是手機或什麼的影像,很模糊,幸而殺卡達菲的時候,有血,卡達菲從坑渠給揪出來,給群眾打死殺死。
我們要有一個怎樣的將來?以怎樣的方式期待將來?
天悅天說,她們面對的只有死亡。
天說在房子的地層,很少下去,有地氈陳舊微霉的味道,所有的舊物她都不丟棄,她讀着信,天悅,天索,天覓,天問,天缺,一個家族的憂鬱信件,豌豆貴族,他們一唯的承傳物是一骨頭微碎的小腳趾,走路的時候,會痛。
天悅買了一雙繡花短皮靴。如果有傷,她要包得好好。天索癌症,天覓癌症,天問癌症,天缺四十三歲的時候,生了一個孩子,孩子鬥雞眼,不會哭泣。
她們沒有在同一個喪禮見過面,總有一個在離開之中。
「我在無人的宿舍讀一篇小說。聖誕快要到了,彷彿也是一個快樂的節日,你生活怎樣麼?什麼時候開始下雪。」天說在酒店房間,天悅坐在床上,房間很小,沒有椅子,兩百歐元一晚的房間,巴黎是個華美牢籠。
天悅站起來。讓我們去喝一杯咖啡。讓我們到街上走走。
這一天突然轉冷,落葉是一天一天的計算,一天稀少,一天承接。
每一次都可以是最後次,天說的完美巨大行李箱,獨居房子,後園的夜合花。肥貓死了以後,天說的房子再也沒有呼喚與氣息,女兒出嫁,丈夫離異,她的臉可以碰到她的腳趾,每一個晚頭黑,天說練習死亡姿勢。
你用怎樣的姿勢離開。天索跪在牀上,算好死。天覓咬傷了舌頭,一口是血,但血不再流。天問,他們將他遺留在一間老人療養病院,五十五歲,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怎樣,只是職員打電話給天缺。
天缺埋怨,你們都跑得遠遠,只有我留在香港,什麼都是我去做,認屍可不是年夜飯,家庭聚會。
留下與離開。我時常猶豫。
「我們所知的有限。」我們所愛也是有限。
天說合上裝滿舊信的盒子。
「一個無手人的寶物盒」,天悅寫。並非天悅知道,她寫姊妹與巴黎的時候,事情還沒有發生。也不是那麼輕佻,「和命運打個照面」,而是物物相承,影影重照。
廣場的人們開始吵架。她老早便知道。路上的人,以為他們是當初與唯一。權力、貪婪、暴烈,從來不會離開人,也即是群眾。自稱理想主義者最大的罪行,是不願意認識自己。
我們從不理想,不可能完美。
知道又怎樣?眼睜睜。知道微塵,並非美德,知道敗壞,損人害己。
我們面對的不過是死亡。世界是他們的,在陰影裏面,以為光明。
停停續續。
天悅在一列從東至西的夜行車,西伯利亞的冬天,窗外的車站如夢,淡藍無月。她醒來。
夜行車一生只有一次,對她來說,穿過冰雪。
頭痛欲裂。愛美莉問,是偏頭痛嗎?如果痛那麼幾天,你要安靜一下嗎?但如果你想,我和湯馬可以和你去看一部電影,回我家,我們弄一個輕沙律吃。
天悅說,我姊妹。
為什麼她要選擇巴黎,會是最後一次嗎?她總是要和我吵架,你是不是見着我才頭痛?為什麼每一次你見到我都鬧幾天的頭痛?我做了什麼?我真那麼令人煩厭嗎?我已經很少很少和你接觸。
接.觸.問題在接觸,一個人,與另一個,面對面,在一間酒店房間。她看着她開始佈滿皺紋的手,她看着自己的手,你的頭,你的灰髮染紅,愛美莉問,是你的妹妹嗎?還是姊姊?
巴黎是一個怎樣的城巿?一個會賣七平方米房子的城巿,七平方米,有沒有廁所那麼大?會有廁所嗎?可以洗澡嗎?幾乎每街都可以聞到尿臭,巴黎的房子沒有廁所嗎?還是他們沒有房子?放尿的人,失意的人,粗魯的人,是嗎?沒有一次沒有在地車給推撞。
天說選擇這一個失意的城巿,完成她的殘缺。這樣還是不要再見面了,我自己去,我去羅浮宮,我去紅磨坊,我坐觀光船,我做所有遊客會做的事情。
天悅說,這好。
情人分手,會說「既然你已經決定」。天悅吃止痛藥,睡覺。
她等待巴黎下雨。天色黯灰。在里斯本買了天使傘子,剛好用。
天悅天說,一次旅遊的相遇,一次母胎的前後巧合,一次斷裂,再一次。
愛丁堡那一次,天悅沒有再聽天說的電話。後來她給她寄去書。
可以選擇的,不是命運,記憶,我們的過去。
為什麼天悅一次又一次的回來到巴黎?離開巴黎以後,她夢到四個人,其中一個人是自己,都踩着狗屎,她說,最後,我們都踩到狗屎。
天說要去巴黎,她無法說你去,你管你去。她鬼迷的回應天說,這你什麼時候去,我五月剛去過,但如果要再去,都可以。
巴黎是一個相遇城巿?頭很痛的時候,天悅在暫時租住的小房子看後園的葉落,一地黃紅灰。灰是巴黎原來的顏色,冬日的開始。
天悅第一個知道的歐洲城巿,是巴黎。那時很年輕。在那間樓頂房間,每天上落七層的迴轉樓梯,她的手按着生鐵把手,涼涼熱熱,涼的是知覺熱的是眼淚,她很年輕便開始長老。
自此她知道,她沒有權利覺得幻滅。這個世界就這是如此模樣,你不喜歡的話,閉嘴,離開。
毁滅她的意志的,不是統治者,或特殊警察。
廣場她後來去過,還是一樣的,有人放風箏,有人騎自行車。一九九七以後,她沒有再去過廣場。後來的人,不大知道廣場發生的事情。給佔領的馬路,她去過,離開以後,佔領者很迷失。和諧廣場,所有的革命群眾和他們要殺死的皇帝一樣,終歸死亡,不見人影人面,憤怒與熱情相若,廣場是香舍麗榭大道的開始,冬日來臨之後,大樹掛滿聖誕裝飾,公園裝置了閃亮的摩天輪,你可以聽到笑聲,人們在這裏尋得他們願意得到的,快樂,華麗,生命感覺。
不比一個摩天輪更多的快樂與華麗。
那間被稱為屎航空公司的小飛機將一群離開巴黎的人,送到南方的西班牙去。飛機着地的時候,乘客拍起手掌來。天悅也跟着拍掌。他們都很高興,天悅笑,終於離開了巴黎。
黃昏入黑,這一晚西維爾古城下雨,星期日晚上,城裏無人。
回到家天悅收到姊姊的電話,她認得電話號碼,她接,問,怎麼了?還在巴黎?做了什麼?天說去了羅浮宮,又問她,頭痛怎樣了?好了些嗎?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天說比天悅聰明。她是對的,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天說比天悅聰明。她是對的,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原載 2014年12月14日《明報》世紀版
明報.世紀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E6%98%8E%E5%A0%B1-%E4%B8%96%E7%B4%80-133035730106880/timeline/
〈陰天,間或有陽光〉 黃碧雲
.jp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1月 24, 2015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1月 24, 2015
Rating:
.jp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1月 24, 2015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1月 24, 2015
Ratin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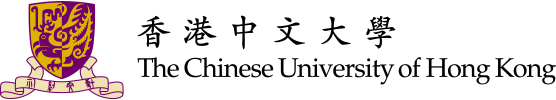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