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變奏篇」
登上967巴士,車內燈火通明,把這黑暗的金融心臟一角照得通體透明。玻璃窗隔開了街上停了又下的雨,漸漸遠去的長江中心前面的沸騰彷彿仍隱約可聞。
登上967巴士,車內燈火通明,把這黑暗的金融心臟一角照得通體透明。玻璃窗隔開了街上停了又下的雨,漸漸遠去的長江中心前面的沸騰彷彿仍隱約可聞。
周五晚上十點半,車上人雖然不少,冷氣還是冷得人直哆嗦,尤其褲管還是濕濕的黏在腿上。兩三個小時前那一場滂沱大雨,即便有備而來,人還是渾身濕透。今年雨水彷彿特別多,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走在街上的日子也多。我們不過是周五傍晚下班出來一下,罷工的碼頭工人卻已經在外面餐風露宿第二十三天了。而他們卻說,大馬路邊上睡帳蓬,比碼頭工作的環境還要好。
剛才我和中大員工總會的同事擠過人群要到台前去,經過工人休息的帳蓬,有工人站到一旁抽煙。昏黃的路燈下這一張張黝黑的臉,平常就生活在我們中間,也許跟我們同擠一輛公車,同吃一家快餐店,同為這城市的高物價所苦。可是,若不是因為這次罷工,我們大概不會進到彼此的視野。要不是因為這次罷工,香港人不會知道,我們引以為傲的碼頭貨運業,工人的工作環境竟然如此惡劣。而我會在周五晚上跑來長江中心撐罷工,並不全是因為我是工會會員。更主要的,是因為我也是工人的女兒,工人的妻子。
父親打仗的時候跟著奶奶走日本仔,從深圳沙井逃難到香港流浮山。奶奶說,母子倆人生地不熟,餓了,只能去海邊的蠔田蠔殼堆裡,撿拾人家挖剩的死蠔肉充饑。母子倆的腳趾各有一隻給蠔殼割傷,嚴重變形。小時候我無法想像逃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看著那從腳面上異軍突起的兩隻腳趾,像兩條僵死的蠕蟲,被封包在傷痕累累的骨肉裡,懵懂間漸漸感知生活的詭異本質。母親是新界圍村女兒,因為家裡兄弟姐妹多,生娘早歿,五六歲就賣給別人當下女,下田種地,上山放牛,沒機會讀書,大字不識一個。兩人各自長大,長大以後還是貧無立錐,走在一起只能繼續胼手胝足。
那是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教科書上說,那時候香港經濟起飛,手工業製造業蓬勃發展,連陳寶珠的電影也高唱「工廠妹萬歲」(《郎如春日風》插曲,1969)。母親的女工生涯並沒有像電影一樣浪漫與光明。母親心靈但手不巧,只能做些低技術的工作,像牛皮廠手襪廠之類。小時候有一段日子,母親回家,指縫間或是手上的傷口上,全都蝕進去藍藍黑黑的顏色,身上還有洗也洗不掉的一陣刺鼻味道。直到長大以後問起母親那雙色彩詭異的手,她才說,那是漂染牛皮的化學藥水,剛開始的時候嗆得人眼淚鼻水直流。而這樣的工作,還是沒法餵飽一家幾口。那時候我們住在母親養娘家親戚廢棄的豬舍裡,前面還有親戚仍然租給別人養豬的豬欄。每天天未亮,母親就去山上那口井挑水給親戚抵房租,偶爾賺點小零錢。然後打發我們上學,自己上工。下工回來又是張羅飯菜家務。我們兄弟姐妹幾個,只能是任意放養長大的。我們家門前除了有豬欄,還有個魚塘。有一次夜裡我去魚塘邊上倒痰罐,失重心掉到水裡,剛好父親在屋外修理東西,看到了把我撈起,我才沒淹死在魚塘的糞水裡。那時候的小孩大概都這樣,沒生病或意外死去的,就長大了。
六七十年代的元朗,除了污染的牛皮廠養豬場,幾乎沒有工業。於是父親得到離家很遠的大角咀五金廠打工,路途遙遠交通不便,車費也高昂,父親只好寄住在工廠,一兩個禮拜才回家一次。家裡大小事,幾乎都是母親獨力扛起。我們兄弟姐妹的童年,幾乎是在父親缺席之下度過的。
沒想到幾十年過去,今天的工人家庭還是無法脫離這父親甚至母親也缺席的命運。臉書上的「大眾碼經」與「碼頭工人的辛酸」社群不斷更新罷工的消息與工人的故事,碼頭裡的揸紙和上水姑爺,貨運旺季要連續三更二十四小時工作,更有連續開工七十二小時的。而和黃高層霍建寧竟然拿自己兒子也每天「自願工作二十小時」云云,來證明碼頭工人必定也是自願加班。沒有比這更涼薄更囂張的管理層。
我想到自己「借證做廠」的童工歲月。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生產旺盛,大批未達法定勞工年齡的女童工借親戚朋友的身分證到工廠打工,我也趕上了這「借證做廠」的尾班車,在深井的九龍紗廠細紗間當養成工。管工也是工人,對我們這些稚氣未脫慌慌張張的女童工,總有幾分體諒與同情,不會特別苛刻。領班多是上海少爺,與工人之間有明顯的階級分野,有時也難免有些下流齷齪的欺壓行為。不過,工錢該多少就多少,勤工津貼加班補水,該給的一分沒少給。大工廠制度深嚴,機器二十四小時運作,工人一天三班輪流工作,八小時分毫不差,開工打卡,遲到扣勤工,沒商量餘地。可冰冷的制度也有人味,會照顧你的肚腸。我們工廠鄰近嘉頓麵包,於是每天每個工人獲發一個嘉頓麵包,由牛皮紙袋發到膠袋包裝,那應該是第一代袋裝麵包了。
除了每天的麵包點心,工廠甚至也照顧工人的住宿,在工廠附近闢地建宿舍,以低廉的租金租給已婚的男女工友安家立戶。我認識的許多已婚工友,就在鐵皮屋大排檔燒鵝店旁邊,在奔流入海的小山溪上游,一邊工作,一邊養兒育女。工廠設廠車,一天三班定點接送不住附近的工人,順路也接送工友的兒女或附近居民的小孩上學。養成工受訓期滿後一年,我申請調到長夜班,晚十一朝七,方便上夜校。每天早上下班,我看著跟我一樣大的學生,穿著整齊校服,背著書包站在廠車走道上,堅毅貞定。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幸福。有幾次我定睛看著她們身上天藍色的制服,直從裡面看出白雲與微風。我真想開口把座位讓給她們,我來替她們站到下車上學去。
麵包、宿舍、小孩上學小方便,自然都是資本家籠絡人心,提高生產力的手段。可是,現在的大資本家連這些小恩小惠都吝嗇,一招外判,把勞動力與資本脫勾,把資方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勞動階層掌握最少社會資源,遇事習慣逆來順受。罷工工友不只一次表示,若非迫不得已,不會走上罷工抗爭這條路。爆發罷工需要鼓一時之勇,能堅持到底,卻需要眾人無比的堅毅與決心。而在政府失效、外判賴皮、大財團無動於衷的情況下,罷工能撐過二十三天以至更久,工友破斧沉舟的決心可以想見。而他們不過想有尊嚴地工作與生活。
有一次我跟丈夫在台灣騎車上桃園縣的拉拉山,經過一條還在建的紅色鋼筋大橋,他告訴我,這就是他當年當扛鐵工建的新巴崚大橋,旁邊的小食攤,便檔一個五十塊台幣吃到飽。台灣夏天中午日頭歹毒,他和工友吃過飯,會在路邊找一處陰涼的地方,舖塊紙皮就席地而睡,躲過了最猛烈的太陽再開工。而他和他的工友們出賣勞力與汗水,也不過想靠自己有尊嚴地生活。我們經過的時候,大橋大概快要竣工了,我們意外地發現,路邊的碎石上果然有工人午睡用的紙皮。會不會就是他睡過的那一張,他的工友沿用至今?
大雨不知道下了多久,終於有稍緩的跡象。台上各個團體、議員輪番上去發言撐工友。大家都感謝工友喚醒了香港人,認清大財閥的醜惡,與跨國資本的冷血。到長毛上台,他一改電視鏡頭前的嚴肅風格,發揮幽默本色,實行向罷工二十三天的工友五體投地扣頭二十三次,以表達對工友的最崇高敬意,動作搞笑,態度卻誠懇真摯。而我們能做的,不過就是這樣那樣地講幾句打氣的話,能力範圍內捐一點小錢,如此而已。
車上我跟同事用手機互傳照片,不知是誰提到今天的日子,我覺得好生眼熟。然後才猛然醒覺,今天是我們結婚周年。已經十一點過了,車才剛過葵涌貨櫃碼頭。不過夜裡交通比較順,只要路上不出狀況,十二點前準能到家,還能趕在午夜前說一句周年快樂。只要路上不出狀況。
〈今年雨水特別多〉陳燕遐(自學中心教師)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9月 01, 2013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9月 01, 2013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9月 01, 2013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9月 01, 2013
Ra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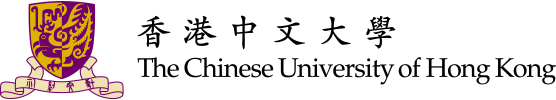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