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文︰梁匡哲;抄寫︰朱昭穎;攝影:吳澄偉】 |
〈有一天,我們會像海一樣生活〉 李昭駿(香港)
我走向碼頭,曾經有過的夜裏
現在,走近海,夜空有時
已不復存在。當我們已經看過
無數的船啟航,回來,明天
黃昏還能偶爾在海面停留,停留在
生活中期待的目光,龐大的慾望都
長得像一扇窗。我們在海一樣
的時間,有着海一樣的疑惑
海一樣地生長,你也許並不喜歡
碼頭一類堅實的詞語,海的背面
是否有着我們的輪廓,有沒有
遺留盛大的宴會與悲哀,抑或
僅僅是城市裏無人曉得的日出,那時候
我們在海裏重生,仰看漁船的網和閃光
更輕易的迷路與感動,簡單的信仰
讓星空和建築在盪漾裏悄然展開
作者李昭駿是一位年輕的90後男詩人,平常我叫他昭仔。
我喜歡這首詩。
她的起句看起來相當平凡:「我走向碼頭,曾經有過的夜裏」。「曾經」一詞攫住我,「曾經有過的夜裏」,其實這個句子具有自反性,「曾經」和「夜裏」將一段時間壓縮在同一個句子,可能是從「夜裏到早上」或是從「下午到夜晚」,伴隨著我「走近」的動作而「離去」。所以,「現在」這個確實的時間指稱就模糊了。這樣的話,「我」感知到時間的流動不是單純的向前,還有經驗裏某種異質性的東西,導向微妙的錯覺(有時已不復存在)。
昭仔對於節奏的掌握頗為成熟,相對於首兩句不動聲色的凝煉,就有鬆開節奏的這句「無數的船啟航,回來,明天」以及跨行部分「黃昏還能偶爾在海面停留」。可是,我彷彿只欣賞到意象,而忘記有關施事者的這句:「當我們已經看過」。這個連句的效果是有趣的,因為它引起我的疑惑:在海面停留的是黃昏,還是船?還是兩者俱是?接續上句,昭仔告訴我們:船和黃昏都有,而重點在於目光本身,它將範圍擴展到各種意義的生活上,甚至是一種有關自我意識,觀看的方式,它的特性是開放性與自由組合。
然後是滿有氣勢的「我們在海一樣/的時間,有着海一樣的疑惑/海一樣地生長」,充分運用海的特性來進行抽象一點的思考。「海一樣的時間」這片語,海一直流動,但流動對海的意義彷彿是虛無的,就像人對於生存這件事,因著這「虛無」而生出「疑惑」。這疑惑是普世性的,像海一樣浸透每個人類,而這些「疑惑」因著生活(或肉體)上的經驗而「生長」,卻像海一樣不帶明顯的意識,它的潮汐漲退總是暗暗地來,暗暗的去。
「你也許並不喜歡/碼頭一類堅實的詞語」,好像岔口的一個句子。起初我並不明白是指甚麼。不過,「碼頭」一詞曾經出現在詩首,而且按照脈絡來看,前面的幾句寫的是「海」。因此容許我大膽想像,這個「你」也是海。那麼整首詩就變成是「我」與「海」的對話,明明知道海不會有任何表示,仍以「我」、「你」和「我們」相稱,顯示彼此的共同的關係,甚至頗有物我交融的況味。「碼頭」可能是我常來的地方,是我記憶中「堅實」的標記,然而「我」很體貼地為你的感受著想,你與我的分歧,也許就是碼頭把「我們」(即海和我)隔開了,不能親密無間地接觸。
於是「海的背面/是否有着我們的輪廓」就更為深刻了。首先,應該沒有人曾經抵達「海的背面」。那麼,為何要提及這個「不存在的地方」?我的想法是,「海的背面」是僅屬你我之間的私密空間,縱然是一個想像的空間,卻於情感上,是「宴會與悲哀」曾經出現之處,它的意義生發於「僅僅是城市裏無人曉得的日出」。雖然日出無人曉得,但正好襯出「我們」曉得的珍貴。「那時候/我們在海裏重生」,陽光灑落在海平面上,展開新的日子,還有零星的漁船作業。這片靜謐的風景沒被打破,卻增添一些生的色彩。
下句將「迷路與感動」並列,還以「簡單的信仰」作類比,我喜歡。如果風景之美不是用來解釋的,而是用來體驗的,同樣地,哪怕是最簡單的信仰,也是個人特殊的體驗。而且往往來得輕易,不需要門檻,不需要更多的智慧,只要全心投入,正如最貧窮與最富有的人都能在信仰裏有領受。而另一方面,信仰有其神秘而不可解釋的部分,如同「感動」之無端而起,「迷路」時乍現的出口。兩者完全可以互通。作者以景結尾,星空和建築,一柔軟一堅硬的,一個自然和人工的物象,在詩裏竟能如此諧協地共存,一起蕩漾,一起展開。可能這就是所謂的真相,造物者從來沒有自私分類。
經歷現代文明的洗禮,人與自然產生不小的斷裂。自然變成人無止境榨取的對象,而人講求效率/工具價值亦導致異化的生活。詩歌的功能之一,就是起碼在意識上與自然重新「復和」。生活是需要想像的,自然提供相當豐富的想像的素材。更有意思的,詩中的時間是徐緩的,非線性的,連接前面的「曾經」,「看過」以及「停留」擬造一種漫步的痕跡(或節奏) ,非以一面倒的正向思考累進,而是清楚展露思考的歷程,當中的疑惑、不完美,甚至矛盾的觀點,他都恰如其分地保留、進而欣賞,最後以盼望回應詩題的願景。
所以我喜歡這首詩,因著她的率真。
生活的想像海,海想像的生活──讀李昭駿〈有一天,我們會像海一樣生活〉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2月 15, 2016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2月 15, 2016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2月 15, 2016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2月 15, 2016
Ra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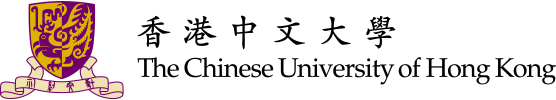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