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文︰梁匡哲;抄寫︰林曉晴;攝影:方嘉誼】 |
〈聲音 I〉 李顥謙(香港)
聲音不來自大鐘,來自沉重的內心
漩渦裏飄浮一根透明的螢火,擦過氣根
天使被投擲。時間正以定期的古音划過水面
房間是白茫的記憶,每天的黑夜都會伸向象牙
疾風在面前,我無法回看那些眼睛的廢墟
而所有的答案都在後面。所有的牆不會倒立。
你迎向我,像所有失落的古書在挑戰我
要反抗。無聲的故事總誘惑我耳邊的暗湧
我在一地絕望的泥濘等候最後的鞭韃
月亮是一塊漁夫的櫻桃,世界如同陀螺
每滴雨就以冷箭潮漲地刺向我。
沒有逃走,沒有人能代替我開門再逃走
直到一種石頭的聲音。大路也在滾動着我
你是我只能使用的隱喻,只能的唯一
繼上次之後,這次介紹另一位90後詩人李顥謙的詩作。
這詩開宗明義地寫「聲音」。
「聲音不來自大鐘,來自沉重的內心」第一句先作出否定然後肯定,它實際提醒讀者們,「大鐘」和「內心」都是聲音可能的源頭,但是當中卻有音量大小的差異,這裏內心勝過了大鐘。於是我們的「著耳點」便由外部的實景引向內部的想像。於內心來說,「漩渦」和「飄浮」均是不明朗的狀態,雖然有「螢火」但是「透明」,擦過突如期來的「氣根」。「天使被投擲」,這個「被」的動態顯示自主性的喪失,即便是「天使」,也只能採用「被投擲」這樣突兀的飛行方式,而不復神聖或優雅。而「時間正以定期的古音划過水面」使我們回到首句的「大鐘」,以及放著大鐘的房間。
「我無法回看那些眼睛的廢墟/而所有的答案都在後面。」
「眼睛的廢墟」似乎是費解的,但如果連上下一句的話,即是「答案」要看見那些「廢墟」才能獲得, 而在眼睛後面支撐著這一切「答案」的,恰恰並不是我們看見的事物,而是一堵牆。「牆」的象徵明顯,代表某種「權力」或更不可動搖的「規範」,這些東西「不會」遷就我們,去「倒立」。
既然如此「要反抗」,「聲音迎向我」,如同「失落的古書在挑戰我」。古書是用眼看的,但若「聲音」是另一些失落的「文字」,以古書艱澀的面貌出現?那麼,就現有的知識來說便是個挑戰,因為他們未必可以卒讀,至少不是「用眼去讀」。
當我們寫到「聲音是怎麼樣的」的時候,不期然地,「無聲的故事總誘惑我耳邊的暗湧」,這是個無邊的誘惑,而很可惜地這個誘惑只是個實現了一半的誘惑:很弔詭,我們只能用文字「紀錄」出現的聲音,卻不能好好地「形容」聲音。所以這些「故事」只能維持著無聲的狀態。
末句「你是我只能使用的隱喻」,更明白的說法該是「我只能使用你作為隱喻」。勉強地接受,是因為找不到更好的代替品,也只能「隱」了。隱喻是「此物比他物」,意即,原本的詞語不足以表達意思,才以另一詞語暫時作表意的輔助。聲音也處於類似的困局,它永遠只能作為隱喻的本體,「聲音」無法言說自身,而這本體先天不足,所以只能「像」其他東西,作為修辭它是尷尬的。這也是為甚麼「沒有逃走,沒有人能代替我開門再逃走」。
這首詩固然有浮燥的地方:「我在一地絕望的泥濘等候最後的鞭韃」,或許過於密集:「每滴雨就以冷箭潮漲地刺向我。」,但他畢竟提出了很好的問題:聲音如何表達自己?
看看我們的語言習慣吧,我們會說:「這件事,你怎樣看」而不是「這件事,你怎樣聽」。我們的電影,配樂只是輔助的,沒有一出戲會單純以聲音當主角。又譬如我們在「看」這首詩的時候,就算是描繪聲音之處(你看,我用的是描繪),用的詞語必須「借用」視象,依附在視象才有空間。又譬如說詩歌中有「圖象詩」,卻沒有專屬聲音的「聲音詩」。(註:陳黎那首著名的〈戰爭進行曲〉雖是圖象詩,卻有意識地結合了視覺與聽覺,嘗試作出這方面的努力)。無疑,詩歌是具有音樂性的,但在實際上必須承認,詩歌的聲音是難以具體分析的,或者應該說,漢語詩關於聲音的批評系統還沒有建立出來,於是常常用「內在音樂性」、「詩無定法」等字眼搪塞過去,聲音的討論變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們說音樂只能說「好聽」、「好正」,相形之下,視覺的詞彙豐富得多。
如果一件事物/事情是立體的,視覺只能提供我們其中一面相的資訊。然而,這是個以視覺主導的社會(我們的文字就首先是視覺的)。 看到甚麼,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的態度與行動。聲音的本質弱勢,但它可以提供另類的想像。因此,除了日常語言系統和文學修辭之張力,其實感受世界的途徑,也是不同感官的較勁之張力中呈現出來。
維特根斯坦說過:「對於不能說的,就應該沉默。」,介於「能說」和「不能說」之間的聲音,是個尚待開發的領域。詩人們打算怎樣做呢,我很感興趣。
用耳朵發現──讀李顥謙〈聲音 I〉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3月 02, 2016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3月 02, 2016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3月 02, 2016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3月 02, 2016
Ra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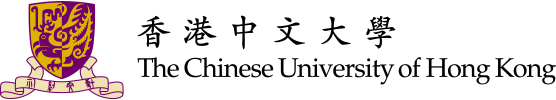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