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熒惑;抄詩及攝影、林沛欣】
|
生離與死別總是人的必經之路,若說悲痛欲絕,莫此為甚。所以我們需要信仰、需要盼望,例如是頭頂之上有一座白雲城堡,我們將來在那重聚細訴當年情;又例如我們不過轉身成為各種生物,繼續在同一顆星球上活著,偶然一隻大斑蝶惘然入室,原來是上世的情人再遇。
對於離別、輪迴,詩人們總是有各種想像,美好或殘忍。東坡居士的明月夜、短松崗,如何想像縱使相逢應不識的悲切,傳誦千載而其哀仍濃烈如新。北島記他父親的詩句似乎另有感悟︰「我回來了——歸程/總是比迷途長/長於一生」。
畢竟亦有比較看得開的,對友人之墓輕怨一句,你卻臥聽著海濤閒話,其實一束紅山茶早已無數次相聚在那寂止的石頭上。至於輪迴,廖偉棠的詩〈白鑽石〉則問起「一個人要有多大的勇氣、/多深的決絕,才能在來生轉世為/亞馬遜森林裡一個低微的生物?」
我們應該回到陳先發的詩裡去。詩人渴望輪迴早來,那是不規則的,也就是說不依常理、甚或是偷渡忘川而去的,而藉著犯禁的輪迴,詩人真正渴望的是重遇他的兄弟姐妹,而那時候他們已經棲居在各種生物之中。我不肯定這些兄弟姐妹是否實指,還是暗指自己的靈魂碎片、或者其實是詩人在投射出他對世間萬物的關懷與大愛?嗯如何解讀自然是留給讀者自由發揮了。
但是不能忘記他開宗明義的傷別。詩人與自己的「兄弟姐妹」分離,因而神傷、冀望相逢,但是他所尋求的完整並不能在當世實現,而是所有他者已經變型。是否因此,他們都不言不語,因為百世千劫過盡,所以大家都疲倦了?還是因為久別,各有追求、各自擁有了新的生活,而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如果轉生成鳥魚是主觀的意願,那就如廖詩所說,是某種不必回頭的決絕了,若在人間世,就是遁入空門、紅塵看破,還有什麼好說呢。如果那些「兄弟姐妹」不過是自己的分身?那同樣令人傷感,難怪雨水無論如何也得落下了。
〈傷別賦〉陳先發
我多麼渴望不規則的輪迴
早點到來,我那些棲居在鸛鳥體內
蟾蜍體內、魚的體內、松柏體內的兄弟姐妹
重聚在一起
大家不言不語,都很疲倦
清瘦頰骨上,披掛著不息的雨水
──陳先發《寫碑之心》(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頁29。
此時此夜難為情──讀陳先發〈傷別賦〉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9月 20, 2015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9月 20, 2015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9月 20, 2015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9月 20, 2015
Ra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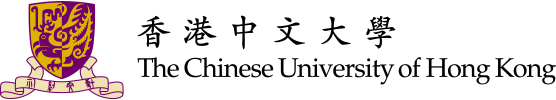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