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值得記下來的事情由中午開始。以前的學生、現在的同事T約吃午飯,因為待他如親弟的F很久沒有和我們──我、黎、朱見面了。F剪了史無前例的短髮,精神很好,行動自如。她說仍要按時做物理治療,練習Reiki(靈氣),但我們看了已放心不少。上次見到F恐怕是去年的清明節前後了。劉教授過世後的頭三年,春秋二祭都由F組織。雖然只是給一眾學生故舊寄發電郵約定日期、預訂素菜午飯、安排開車和買祭品的人手,剛過去的清明節她身體不好,春祭就辦不起來了。去年重陽節F患了感冒,臨時不能出發,但因為已為我們安排停當,所以秋祭如常舉行。
F是劉教授學生的學生,所以稱劉教授為師公。十多年前吧,F在美國得到博士候選人資格,回到香港撰寫論文,老師介紹她給師公認識。大概是那一年,我在劉教授的生日會上第一次和她見面。後來劉教授的柏金遜症愈來愈嚴重,很少離開大學宿舍,定期覆診和突然不適都由F一力照顧,直至2010年過世。在劉教授最後的十多年裡,F是他最重要的保護者。即使身後又何嘗不是?有一年拜祭之前,曾經照料劉教授的泰籍女傭夢見劉教授對說椅子壞了,F和T竟在一家大埔的香燭店找到紙糊的按摩椅子祭品,還買了兩張不同款式的。劉教授安然度過他最後的日子後,F的脊骨才出問題,那段日子是劉教授本人的福氣,還是F沾了劉教授的福氣,我不敢說,但也禁不住想。
幸好這次見面,F的聲音響亮仍如以往,看來物理治療效果不錯。她說希望定期見面,好令養病生涯有點趣味。我想到多年前有一次F去旅行,囑咐我多點看望劉教授。那時劉教授腦子仍舊清楚,但說話開始有困難了,我們談不了甚麼,和他一同坐在客廳裡,心裡記掛着種種待辦的事情,時間過得特別慢。告辭時劉教授問甚麼時候會再見,我含糊地說過兩天吧──事實上恐怕是不止三四天。這事情說要內疚有點誇張,但就憑每天無倦無厭地探望,F的了不起就很顯然了。
午飯後回到家裡,繼續做一會不值得記、也記不起來的事情,無非是回覆一些公務電郵、寫一些沒有甚麼用處的文書吧,反正是每天都在做的那些事情。四時三刻再度離家。這天非常熱,預計晚上在維園一定很辛苦,但今年的形勢又不容示弱。為免像去年那樣,由於到得太晚,沒有坐的地方,也聽不到廣播,只能默默站到完場,決意早點動身。可是我們還想先到銅鑼灣的韓國觀光公社拿些旅遊資料,再加上吃晚飯,其實時間不見得充裕。
畢竟離八點晚會開場還有一段時間,港鐵裡穿黑色的人不多。一抬頭,黑衣黑褲,頸上掛了一部徠卡小型定焦照相機的廖份外矚目。跟他打個招呼,他說先到東角道拍攝街頭音樂會,再進維園。我向他介紹身旁的田泥,他說不知道我結了婚,我說快十年了,他說他也差不多。現在有了孩子,雖然是無業遊民,也忙得不可開交。孩子一歲半,最近肯讓祖母帶,他才騰得出一點空餘時間,做些其他事情,例如拍攝這個晚上。但孩子非常好動,大異於父母,老人家看管起來也頗費力。田泥問他照相機好不好用,他說好,但很貴,又拿出另一支定焦鏡頭讓我們一開眼界。
一同在銅鑼灣站下了車,各自從不同出口離去,一下子就在人潮中沒頂。剛好趕及在韓國觀光公社關門前到達,但取得的資料不多,我們隨便走進世貿中心一家日式西餐廳吃一頓提早的晚飯。飯後只是七時左右,田泥聽說每年這段日子時代廣場的藝術展覽都有點隱義,我們想一探究竟,於是繞到那邊看看,順便上洗手間。這一期是韓國藝術家朴善基和姜錫鉉的雙人展,首先看到廣場外的奔馬雕塑,我數一數,合共五匹,算不上是六四的暗示吧,二樓大堂的展品也不像有甚麼玄機。距離吃完飯不久,上一次洗手間沒有甚麼用,這當然是我一向的焦慮。
終於進入維園了。因為到得較早,能夠坐在最後一個足球場的第一行,側面是向高士威道的出口。坐下來不久,有人來派洋燭,不一會又借到了火,靜靜等候晚會開始。回頭一望,這最後一個球場也坐滿了。八時正,大會宣佈程序開始,熟悉的音樂奏起,突然強風颯颯,吹過一些樹葉,夾着雨粉。我們早有準備,張開一把傘。雨漸大,再開一把。轉瞬間,地面濕得坐不住了。站起來,雨勢愈來愈大,褲管全濕,水浸到鞋子的一半高度,我把背包反背在胸前,廣播突然中斷了,心想莫不是老天也要維園晚會二十三年來第一次辦不成吧,我們一定要堅持。傾瀉的雨水像要把我們的傘骨硬生生淋斷,維園裡集結的人會因為急着避雨而互相踐踏嗎?決心在十分鐘內就給恐懼沖決了。隨着及早離開的人群步向出口,回頭一瞥,深感實在太對不起裡面的人了。
高士威道東行線上本有直接回家的巴士站,但走了幾步,前面已擠滿了人,右邊剛好是過路處,來不及多想就往人少的方向走。對面馬路停了一輛112號巴士,我們跳上去。上層乘客不多,空調冷颼颼的,幸而帶了風衣和外套。巴士從高士威道轉入怡和街,在下一站停了很久,我還擔心是不是機件故障。終於我們在紅磡海底隧道出口下車,轉乘火車回家。到得家裡,差不多九時半,洗過熱水澡,歪在椅子上看電視新聞,才知道燭光晚會延續到半小時前才結束,有些人待雨勢轉弱又回到維園裡。
打開電腦,收到台灣朋友阿冠的電郵。兩天前南投地震,我寄了幾封電郵問候那邊的相識,可幸迅速得到平安的回音。阿冠的回郵說:「香港沒有地震的威脅,不會不時讓人提心吊膽一番,真是好山好水!」我向來悲觀,忍不住回他說:「香港天災不多,但社會壓抑不小,星期二的六四晚會有多少人出席,可能就是形勢變化的指標了。」阿冠最新的電郵說:「看『主場新聞』的報導,今晚晚會看來還是人潮洶湧,雖有大雨,但怎麼也驅不散人群,真是令人振奮!」已經是翌日的零時三十三分了,但這尾巴怎能不記下來呢。我這樣回覆:「你也看『主場新聞』!我和田泥提早在七點半坐到維園裏,以免重蹈去年擠在外圍甚麼都聽不到看不見的覆轍。誰知晚會八點剛開始時,就下起大雨,撐了傘也沒用,轉瞬間地上漲了幾吋高的水。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坐在場邊自己帶來的矮凳上,好像被洪水圍困的樣子。其他人互相借火,重燃吹熄了的蠟燭。但雨勢愈來愈大,大會的音響也停止了,我們決定離場。僅僅走到對面馬路巴士站的幾分鐘路程,衣褲都已濕透。回家後看電視,才知道不少人堅持留下,有些人則待雨勢轉弱又回到場中。今年維園的俯瞰照特別漂亮,因為大部份人撐着傘,遠鏡下別有一種往年所無的繽紛色彩。」
F是劉教授學生的學生,所以稱劉教授為師公。十多年前吧,F在美國得到博士候選人資格,回到香港撰寫論文,老師介紹她給師公認識。大概是那一年,我在劉教授的生日會上第一次和她見面。後來劉教授的柏金遜症愈來愈嚴重,很少離開大學宿舍,定期覆診和突然不適都由F一力照顧,直至2010年過世。在劉教授最後的十多年裡,F是他最重要的保護者。即使身後又何嘗不是?有一年拜祭之前,曾經照料劉教授的泰籍女傭夢見劉教授對說椅子壞了,F和T竟在一家大埔的香燭店找到紙糊的按摩椅子祭品,還買了兩張不同款式的。劉教授安然度過他最後的日子後,F的脊骨才出問題,那段日子是劉教授本人的福氣,還是F沾了劉教授的福氣,我不敢說,但也禁不住想。
幸好這次見面,F的聲音響亮仍如以往,看來物理治療效果不錯。她說希望定期見面,好令養病生涯有點趣味。我想到多年前有一次F去旅行,囑咐我多點看望劉教授。那時劉教授腦子仍舊清楚,但說話開始有困難了,我們談不了甚麼,和他一同坐在客廳裡,心裡記掛着種種待辦的事情,時間過得特別慢。告辭時劉教授問甚麼時候會再見,我含糊地說過兩天吧──事實上恐怕是不止三四天。這事情說要內疚有點誇張,但就憑每天無倦無厭地探望,F的了不起就很顯然了。
午飯後回到家裡,繼續做一會不值得記、也記不起來的事情,無非是回覆一些公務電郵、寫一些沒有甚麼用處的文書吧,反正是每天都在做的那些事情。四時三刻再度離家。這天非常熱,預計晚上在維園一定很辛苦,但今年的形勢又不容示弱。為免像去年那樣,由於到得太晚,沒有坐的地方,也聽不到廣播,只能默默站到完場,決意早點動身。可是我們還想先到銅鑼灣的韓國觀光公社拿些旅遊資料,再加上吃晚飯,其實時間不見得充裕。
畢竟離八點晚會開場還有一段時間,港鐵裡穿黑色的人不多。一抬頭,黑衣黑褲,頸上掛了一部徠卡小型定焦照相機的廖份外矚目。跟他打個招呼,他說先到東角道拍攝街頭音樂會,再進維園。我向他介紹身旁的田泥,他說不知道我結了婚,我說快十年了,他說他也差不多。現在有了孩子,雖然是無業遊民,也忙得不可開交。孩子一歲半,最近肯讓祖母帶,他才騰得出一點空餘時間,做些其他事情,例如拍攝這個晚上。但孩子非常好動,大異於父母,老人家看管起來也頗費力。田泥問他照相機好不好用,他說好,但很貴,又拿出另一支定焦鏡頭讓我們一開眼界。
一同在銅鑼灣站下了車,各自從不同出口離去,一下子就在人潮中沒頂。剛好趕及在韓國觀光公社關門前到達,但取得的資料不多,我們隨便走進世貿中心一家日式西餐廳吃一頓提早的晚飯。飯後只是七時左右,田泥聽說每年這段日子時代廣場的藝術展覽都有點隱義,我們想一探究竟,於是繞到那邊看看,順便上洗手間。這一期是韓國藝術家朴善基和姜錫鉉的雙人展,首先看到廣場外的奔馬雕塑,我數一數,合共五匹,算不上是六四的暗示吧,二樓大堂的展品也不像有甚麼玄機。距離吃完飯不久,上一次洗手間沒有甚麼用,這當然是我一向的焦慮。
終於進入維園了。因為到得較早,能夠坐在最後一個足球場的第一行,側面是向高士威道的出口。坐下來不久,有人來派洋燭,不一會又借到了火,靜靜等候晚會開始。回頭一望,這最後一個球場也坐滿了。八時正,大會宣佈程序開始,熟悉的音樂奏起,突然強風颯颯,吹過一些樹葉,夾着雨粉。我們早有準備,張開一把傘。雨漸大,再開一把。轉瞬間,地面濕得坐不住了。站起來,雨勢愈來愈大,褲管全濕,水浸到鞋子的一半高度,我把背包反背在胸前,廣播突然中斷了,心想莫不是老天也要維園晚會二十三年來第一次辦不成吧,我們一定要堅持。傾瀉的雨水像要把我們的傘骨硬生生淋斷,維園裡集結的人會因為急着避雨而互相踐踏嗎?決心在十分鐘內就給恐懼沖決了。隨着及早離開的人群步向出口,回頭一瞥,深感實在太對不起裡面的人了。
高士威道東行線上本有直接回家的巴士站,但走了幾步,前面已擠滿了人,右邊剛好是過路處,來不及多想就往人少的方向走。對面馬路停了一輛112號巴士,我們跳上去。上層乘客不多,空調冷颼颼的,幸而帶了風衣和外套。巴士從高士威道轉入怡和街,在下一站停了很久,我還擔心是不是機件故障。終於我們在紅磡海底隧道出口下車,轉乘火車回家。到得家裡,差不多九時半,洗過熱水澡,歪在椅子上看電視新聞,才知道燭光晚會延續到半小時前才結束,有些人待雨勢轉弱又回到維園裡。
打開電腦,收到台灣朋友阿冠的電郵。兩天前南投地震,我寄了幾封電郵問候那邊的相識,可幸迅速得到平安的回音。阿冠的回郵說:「香港沒有地震的威脅,不會不時讓人提心吊膽一番,真是好山好水!」我向來悲觀,忍不住回他說:「香港天災不多,但社會壓抑不小,星期二的六四晚會有多少人出席,可能就是形勢變化的指標了。」阿冠最新的電郵說:「看『主場新聞』的報導,今晚晚會看來還是人潮洶湧,雖有大雨,但怎麼也驅不散人群,真是令人振奮!」已經是翌日的零時三十三分了,但這尾巴怎能不記下來呢。我這樣回覆:「你也看『主場新聞』!我和田泥提早在七點半坐到維園裏,以免重蹈去年擠在外圍甚麼都聽不到看不見的覆轍。誰知晚會八點剛開始時,就下起大雨,撐了傘也沒用,轉瞬間地上漲了幾吋高的水。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坐在場邊自己帶來的矮凳上,好像被洪水圍困的樣子。其他人互相借火,重燃吹熄了的蠟燭。但雨勢愈來愈大,大會的音響也停止了,我們決定離場。僅僅走到對面馬路巴士站的幾分鐘路程,衣褲都已濕透。回家後看電視,才知道不少人堅持留下,有些人則待雨勢轉弱又回到場中。今年維園的俯瞰照特別漂亮,因為大部份人撐着傘,遠鏡下別有一種往年所無的繽紛色彩。」
〈六四二十四〉樊善標(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87年畢業)
![〈六四二十四〉樊善標(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87年畢業)]()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8月 10, 2013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8月 10, 2013
Ra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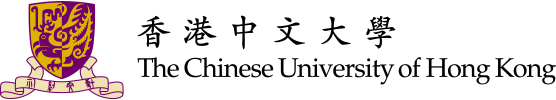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