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文系的蔡少鋒寫了藏在一首詩裡,詩人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作為旁觀的我們,當然無由得知這秘密的來龍去脈,不過,光看一首詩與一個詩人的成長,以及往來其中古今中外的名角,也是樂事一樁。
****************************************************************************
And I am dumb to tell a weather's wind
How time has ticked a heaven round the stars.
-- Dylan Thomas
- 1 -
二零零八年暑假,得悉著名詩人北島在大學開了一個暑期課程「中英詩歌譯作坊」。我英文不好,但我知道這樣的機會不可多得,就興匆匆的報名了。沒想 到老師是那麼溫柔而且敦厚的一位長者,我們熟悉的都是他在壯歲寫下的詩句,那些句子慷慨激昂之處我一直以為堪比漢魏詩的「風骨」。老師說課程主要以他的詩 歌翻譯隨筆《時間的玫瑰》為教材,第一課談的是威爾士詩人狄蘭.湯馬士(Dylan Thomas, 1914-1953)。他著我們嘗試翻譯狄蘭.湯馬士的一首詩──〈通過綠色導火索催開花朵的力量〉(“The force that through the green fuse drives the flower”)。我英文不好,譯得好吃力,但也懂得這首詩的一些好處。譬如說詩中驚人的意象,奇妙的節奏。對,節奏是奇妙的──老師給我們播放狄蘭.湯 馬士的詩歌朗誦錄音聲帶,可惜我沒有英文文學的底子,就不知其所以然了。
老師說,課程的習作除了翻譯外,還要作一首詩,第二堂拿出來討論。回家以後是夜晚了,香港的暑假炎熱而多雨,我進大學後以學業和兼職兩忙,創作的 觸覺也遲鈍了許多。那時候家仍在葵涌的舊居,車喧塵多,下雨天可是我所喜愛的天氣。我敲打筆記本電腦的鍵盤,作了一首題為〈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的十七行 短詩: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我選擇在街心放棄了雨傘
任由一切發生
而最後只落得一身狼狽
如蝸牛在葉子上留下的曖昧
濕漉漉的外衣冷而且緊
夜色矇矓,黑暗遂顯得龐大
我知道水流披面的寧靜
只在閉目的一瞬間凝結
開眼以後我將迎來雨水的酸澀
在牆角獨處的雨傘怎樣看
也覺得老邁,窗外虛偽的風景
我知道黑夜需要雨水伴奏
斷續的節拍
我不會想起日間無聊的鬧哄
天氣報告說明日天晴
別忘了把今晚的影子曬乾
- 2 -
大二升大三那年的暑假無疑是快樂的,只可惜太短了些──我修了兩個暑期課程,做好功課和論文都快九月了,要趕開學的各樣事宜。而每年大學開學最讓人愉快的,無非是八月的迎新營吧。
剛入學時候是「組仔」,大一暑假可輪到我當迎新營的「搞手」了。因為家事錯過了迎新營籌委(俗稱「OC」)的第一次會議,回到中大開會的時候,籌 委們都基本選好了各自的位置──內務部、外務部丶節目部,還有最忙碌的行政部。我問友好的同伴,他們說已經為我預留節目部的位置,而行政部的「文書」位置 仍然懸空。我想進入行政部幫忙,但按歷年慣例是行政部文書由內務部部員擔當,而內務部已經滿員了。我不禁錯愕,這規矩誰定的?我提出疑問,因為籌委們都是 一年來朝夕相見的同窗,於是求仁得仁,我當上行政部文書,兼任節目部文書。
二零零七年,颱風照常在迎新營期間襲港。傳說那年中文系有一個迎新營籌委因天雨路滑加兼連日睡眠不足,在潤昌堂外的石地失足滑倒。他手腳也流著 血,額頭也破損了,卻因為要趕著把一張紙條交給另一位籌委,告知對方下一個遊戲環節的步驟,於是他在雨中繼續奔跑……回到潤昌堂,等了良久,終於有懂急救 的輔導員(俗稱「組爸/媽」)幫忙急救包綳帶。下一組來潤昌堂遊戲的新生到了,剛好受傷的籌委是要在迎新營的遊戲環節兼演木乃伊的角色,於是他一邊給包紮 綳帶,一邊笑著告訴來玩遊戲的新生遊戲的步驟。他們吃驚的看著他說:「嘩,怎麼可以造到這麼逼真的鮮血呢?」受傷的籌委只好笑著回答:「當然啦,我們中文 系學生可是很厲害的。」於是那個貌不驚人的迎新營籌委就這樣在系內「成名」了,去威爾斯急症室的路可比終南山的便捷多了。
但八號颱風下的中大,等候一輛救傷車要多少時間呢?於是同伴趕忙過來,一個打電話找的士,一個找來食物,一個扶著他走到新亞的知行樓歇息。他們不 知道,幾個小時以前,他和另一位同伴,就在知行樓的大堂,通宵討論人生道路的問題……他問他,在校園裏以「詩人」之名遊逛了一整個學年,究竟每日每夜掛在 嘴邊的「詩集」甚麼時候可以付梓呢?他說,和中學時代的友人約定好了,在二十五歲以前會完成這一個夢想的。「詩人」和同伴二人看著知行樓大堂窗外吐露港縹 緲的水色,那時候是很難說服他們相信「詩集」不可能在旦夕之間完成的。
好容易等到一輛的士來到。一位同伴陪受傷的迎新營籌委上車,匆忙趕到威爾斯的急症室。大概是連日睡眠不足的緣故吧,當護士詢問傷者住址的時候,迎新營籌委沒頭沒腦的接上一句「馮景禧樓」。護士不解,傷者旁邊的同伴哭笑不得的代答,馮景禧樓是中大文學院的辦公室所在哩。
- 3 -
相比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的夏天無疑是愉快的。準備升大三的我不再需要為籌備迎新營的事奔波了,可以在美麗的大學校園四處遊逛,可以讀一些自己 想讀的書,也杜絕在雨中跑步並且失足的可能。我修了一門歷史系的課,為下一個學年申請副修歷史系作準備,是張學明教授的比較史專題課,主題是討論世界神 話。我最後的成績當然不忍卒睹——雖說文史哲在中國學術界本為一家,但一個世紀以來的西學影響下,中文系學生要兼通史學,無疑是吃力不討好的。幸而那個暑 假還有北島老師的詩歌課。
第二堂,詩寫好了,我們回到鄭棟材樓的教室。老師先著我們討論一些國內外學者的唐詩英譯,才談我們自己在家裏寫好的詩稿──老師大概聽不懂我過分 「地道」的外語,悄悄把授課語言由英語「微調」為普通話了──是啊,我真的記不清楚「沙漠」和「甜品」的差別,老師笑著提點我下次可以帶電子辭典回來上 課;我笑得比鴕鳥燦爛,因為我蹩腳的英語可以藏在甜甜的沙子中了。
老師讓我們輪流朗讀自己的詩。我一邊期期艾艾的用普通話唸一遍,一邊偷看老師和同學的表情──他們好專注的在聽哩,這是我前所未有的經歷。老師好 奇的是我詩中意象的組合,他問我為甚麼會想到「蝸牛」呢?中大的山路可多蝸牛啊,尤其是聯合書院一帶。同學好奇的是我怎麼會想到以「天氣報告」作結,其實 說穿了就毫不希奇——二零零八年的香港,「功能電話」還未被「智能電話」取代,炎熱多雨的夏天,出門前總得看看天氣先生的消息,並且帶一把雨傘傍身——雨 傘可是中文系迎新營著名的「中大三寶」之一哩。我們幾個同學愉快地交流彼此的意見,回家以後又修改各自的詩作,準備下一回的討論。
- 4 -
經過一個月的討論和修改,我們在「譯作坊」的最後一課輪番朗讀自己的詩作「定稿」。我的定稿與初稿的相同之處,除了題目以外,大概就是不足為外人道的節奏吧。我問老師可以用我最純熟的廣東話朗讀嗎?老師點頭說可以。
那首詩我一直好喜歡,後來刊登在該年十月《秋螢》復活號第六十四期: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陽光都給那些大廈吸走了
人只能永恆在黑夜漂流
今晚你以逃離作委身的浮木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穿過千個漏壺陽光灑出
黑色的雨水灌溉柏油大地
你更喜歡不喝水的花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街道上牆壁砌出的避風港
一再排演拒絕者的戲
你更喜歡靜止的風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家裏總有一輪太陽懸掛
- 5 -
二零一二年七月,我像一朵浮雲般飄回中大著名的「百萬大道」上。大道上拍照的人比到圖書館還書的人更多,我手上的書本還未過期,便找來旁人幫忙拍 照。平板電腦真的好方便,「咔嚓」以後便可以立時傳上社交網絡。喲,不意社交網絡上的朋友都事忙,吃完一頓下午茶也還沒有騙到朋友「讚好」。是啦,本科以 後,原來唸詩填詞的五陵少年也得為衣食四出奔波。宋詞裏有一個名句——「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和月。」語氣何其瀟灑,但我們都知道作者歐陽修是婉約 派的名家。
高興的是大學生的暑假,本部仍然有美好的咖啡閣(Coffee Corner)為我這種閑適的路人開放,更讓我驚喜的碰上系主任何教授。我和教授有半年沒打過照面了,離大二那年的莊子課,更有四年之遙。互道寒暄實在毫 無道家的灑脫,但我實在只懂羞答答的打招呼。教授問我:你怎麼迷上托利斯(Fernando Torres, 1984- )了?夏日炎炎,那天我正穿著一件薄薄的白色T-shirt,衫上燙了一個顯眼的車路士(Chelsea FC)會徽。我告訴教授我喜歡車路士,而沒有告訴他其實我也很喜歡托利斯。
中大校園的風光還是那樣的明媚,並沒有因為雙軌年的來臨而轉變。初進研究院的這一年,我常遊走中大本部和聯合、新亞一帶,不意發現校園裏悄悄出現 了手抄詩歌的橫條和黑板。後來得知是「書寫力量」的手筆,驚喜不已。可恨本科畢業以後詩筆遲滯,我似乎不再得到繆思的垂幸,睡夢中常憂慮郭璞有天會過來沒 收我的五彩筆,一如曾經笑傲六朝的江淹。十一月,我把幾年前的舊作寄給「書寫力量」,那首詩就是「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的初稿。榮幸詩作得到「書寫力量」 選中,抄寫並印製為明信片。
我和曩昔的同伴談起這首詩,他們好奇的是我為甚麼不把當年的「定稿」寄給「書寫力量」,偏偏選了一首藏在抽屜裏發霉的「初稿」。這當然是「詩人」們的秘密,不可以道破,像洛夫在〈與李賀共飲〉中所說的:「不懂就讓他們去不懂/不懂/為何我們讀後相視大笑」。
(二零一三年六月)
****************************************************************************
And I am dumb to tell a weather's wind
How time has ticked a heaven round the stars.
-- Dylan Thomas
- 1 -
二零零八年暑假,得悉著名詩人北島在大學開了一個暑期課程「中英詩歌譯作坊」。我英文不好,但我知道這樣的機會不可多得,就興匆匆的報名了。沒想 到老師是那麼溫柔而且敦厚的一位長者,我們熟悉的都是他在壯歲寫下的詩句,那些句子慷慨激昂之處我一直以為堪比漢魏詩的「風骨」。老師說課程主要以他的詩 歌翻譯隨筆《時間的玫瑰》為教材,第一課談的是威爾士詩人狄蘭.湯馬士(Dylan Thomas, 1914-1953)。他著我們嘗試翻譯狄蘭.湯馬士的一首詩──〈通過綠色導火索催開花朵的力量〉(“The force that through the green fuse drives the flower”)。我英文不好,譯得好吃力,但也懂得這首詩的一些好處。譬如說詩中驚人的意象,奇妙的節奏。對,節奏是奇妙的──老師給我們播放狄蘭.湯 馬士的詩歌朗誦錄音聲帶,可惜我沒有英文文學的底子,就不知其所以然了。
老師說,課程的習作除了翻譯外,還要作一首詩,第二堂拿出來討論。回家以後是夜晚了,香港的暑假炎熱而多雨,我進大學後以學業和兼職兩忙,創作的 觸覺也遲鈍了許多。那時候家仍在葵涌的舊居,車喧塵多,下雨天可是我所喜愛的天氣。我敲打筆記本電腦的鍵盤,作了一首題為〈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的十七行 短詩: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我選擇在街心放棄了雨傘
任由一切發生
而最後只落得一身狼狽
如蝸牛在葉子上留下的曖昧
濕漉漉的外衣冷而且緊
夜色矇矓,黑暗遂顯得龐大
我知道水流披面的寧靜
只在閉目的一瞬間凝結
開眼以後我將迎來雨水的酸澀
在牆角獨處的雨傘怎樣看
也覺得老邁,窗外虛偽的風景
我知道黑夜需要雨水伴奏
斷續的節拍
我不會想起日間無聊的鬧哄
天氣報告說明日天晴
別忘了把今晚的影子曬乾
- 2 -
大二升大三那年的暑假無疑是快樂的,只可惜太短了些──我修了兩個暑期課程,做好功課和論文都快九月了,要趕開學的各樣事宜。而每年大學開學最讓人愉快的,無非是八月的迎新營吧。
剛入學時候是「組仔」,大一暑假可輪到我當迎新營的「搞手」了。因為家事錯過了迎新營籌委(俗稱「OC」)的第一次會議,回到中大開會的時候,籌 委們都基本選好了各自的位置──內務部、外務部丶節目部,還有最忙碌的行政部。我問友好的同伴,他們說已經為我預留節目部的位置,而行政部的「文書」位置 仍然懸空。我想進入行政部幫忙,但按歷年慣例是行政部文書由內務部部員擔當,而內務部已經滿員了。我不禁錯愕,這規矩誰定的?我提出疑問,因為籌委們都是 一年來朝夕相見的同窗,於是求仁得仁,我當上行政部文書,兼任節目部文書。
二零零七年,颱風照常在迎新營期間襲港。傳說那年中文系有一個迎新營籌委因天雨路滑加兼連日睡眠不足,在潤昌堂外的石地失足滑倒。他手腳也流著 血,額頭也破損了,卻因為要趕著把一張紙條交給另一位籌委,告知對方下一個遊戲環節的步驟,於是他在雨中繼續奔跑……回到潤昌堂,等了良久,終於有懂急救 的輔導員(俗稱「組爸/媽」)幫忙急救包綳帶。下一組來潤昌堂遊戲的新生到了,剛好受傷的籌委是要在迎新營的遊戲環節兼演木乃伊的角色,於是他一邊給包紮 綳帶,一邊笑著告訴來玩遊戲的新生遊戲的步驟。他們吃驚的看著他說:「嘩,怎麼可以造到這麼逼真的鮮血呢?」受傷的籌委只好笑著回答:「當然啦,我們中文 系學生可是很厲害的。」於是那個貌不驚人的迎新營籌委就這樣在系內「成名」了,去威爾斯急症室的路可比終南山的便捷多了。
但八號颱風下的中大,等候一輛救傷車要多少時間呢?於是同伴趕忙過來,一個打電話找的士,一個找來食物,一個扶著他走到新亞的知行樓歇息。他們不 知道,幾個小時以前,他和另一位同伴,就在知行樓的大堂,通宵討論人生道路的問題……他問他,在校園裏以「詩人」之名遊逛了一整個學年,究竟每日每夜掛在 嘴邊的「詩集」甚麼時候可以付梓呢?他說,和中學時代的友人約定好了,在二十五歲以前會完成這一個夢想的。「詩人」和同伴二人看著知行樓大堂窗外吐露港縹 緲的水色,那時候是很難說服他們相信「詩集」不可能在旦夕之間完成的。
好容易等到一輛的士來到。一位同伴陪受傷的迎新營籌委上車,匆忙趕到威爾斯的急症室。大概是連日睡眠不足的緣故吧,當護士詢問傷者住址的時候,迎新營籌委沒頭沒腦的接上一句「馮景禧樓」。護士不解,傷者旁邊的同伴哭笑不得的代答,馮景禧樓是中大文學院的辦公室所在哩。
- 3 -
相比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的夏天無疑是愉快的。準備升大三的我不再需要為籌備迎新營的事奔波了,可以在美麗的大學校園四處遊逛,可以讀一些自己 想讀的書,也杜絕在雨中跑步並且失足的可能。我修了一門歷史系的課,為下一個學年申請副修歷史系作準備,是張學明教授的比較史專題課,主題是討論世界神 話。我最後的成績當然不忍卒睹——雖說文史哲在中國學術界本為一家,但一個世紀以來的西學影響下,中文系學生要兼通史學,無疑是吃力不討好的。幸而那個暑 假還有北島老師的詩歌課。
第二堂,詩寫好了,我們回到鄭棟材樓的教室。老師先著我們討論一些國內外學者的唐詩英譯,才談我們自己在家裏寫好的詩稿──老師大概聽不懂我過分 「地道」的外語,悄悄把授課語言由英語「微調」為普通話了──是啊,我真的記不清楚「沙漠」和「甜品」的差別,老師笑著提點我下次可以帶電子辭典回來上 課;我笑得比鴕鳥燦爛,因為我蹩腳的英語可以藏在甜甜的沙子中了。
老師讓我們輪流朗讀自己的詩。我一邊期期艾艾的用普通話唸一遍,一邊偷看老師和同學的表情──他們好專注的在聽哩,這是我前所未有的經歷。老師好 奇的是我詩中意象的組合,他問我為甚麼會想到「蝸牛」呢?中大的山路可多蝸牛啊,尤其是聯合書院一帶。同學好奇的是我怎麼會想到以「天氣報告」作結,其實 說穿了就毫不希奇——二零零八年的香港,「功能電話」還未被「智能電話」取代,炎熱多雨的夏天,出門前總得看看天氣先生的消息,並且帶一把雨傘傍身——雨 傘可是中文系迎新營著名的「中大三寶」之一哩。我們幾個同學愉快地交流彼此的意見,回家以後又修改各自的詩作,準備下一回的討論。
- 4 -
經過一個月的討論和修改,我們在「譯作坊」的最後一課輪番朗讀自己的詩作「定稿」。我的定稿與初稿的相同之處,除了題目以外,大概就是不足為外人道的節奏吧。我問老師可以用我最純熟的廣東話朗讀嗎?老師點頭說可以。
那首詩我一直好喜歡,後來刊登在該年十月《秋螢》復活號第六十四期: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陽光都給那些大廈吸走了
人只能永恆在黑夜漂流
今晚你以逃離作委身的浮木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穿過千個漏壺陽光灑出
黑色的雨水灌溉柏油大地
你更喜歡不喝水的花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街道上牆壁砌出的避風港
一再排演拒絕者的戲
你更喜歡靜止的風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家裏總有一輪太陽懸掛
- 5 -
二零一二年七月,我像一朵浮雲般飄回中大著名的「百萬大道」上。大道上拍照的人比到圖書館還書的人更多,我手上的書本還未過期,便找來旁人幫忙拍 照。平板電腦真的好方便,「咔嚓」以後便可以立時傳上社交網絡。喲,不意社交網絡上的朋友都事忙,吃完一頓下午茶也還沒有騙到朋友「讚好」。是啦,本科以 後,原來唸詩填詞的五陵少年也得為衣食四出奔波。宋詞裏有一個名句——「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和月。」語氣何其瀟灑,但我們都知道作者歐陽修是婉約 派的名家。
高興的是大學生的暑假,本部仍然有美好的咖啡閣(Coffee Corner)為我這種閑適的路人開放,更讓我驚喜的碰上系主任何教授。我和教授有半年沒打過照面了,離大二那年的莊子課,更有四年之遙。互道寒暄實在毫 無道家的灑脫,但我實在只懂羞答答的打招呼。教授問我:你怎麼迷上托利斯(Fernando Torres, 1984- )了?夏日炎炎,那天我正穿著一件薄薄的白色T-shirt,衫上燙了一個顯眼的車路士(Chelsea FC)會徽。我告訴教授我喜歡車路士,而沒有告訴他其實我也很喜歡托利斯。
中大校園的風光還是那樣的明媚,並沒有因為雙軌年的來臨而轉變。初進研究院的這一年,我常遊走中大本部和聯合、新亞一帶,不意發現校園裏悄悄出現 了手抄詩歌的橫條和黑板。後來得知是「書寫力量」的手筆,驚喜不已。可恨本科畢業以後詩筆遲滯,我似乎不再得到繆思的垂幸,睡夢中常憂慮郭璞有天會過來沒 收我的五彩筆,一如曾經笑傲六朝的江淹。十一月,我把幾年前的舊作寄給「書寫力量」,那首詩就是「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的初稿。榮幸詩作得到「書寫力量」 選中,抄寫並印製為明信片。
我和曩昔的同伴談起這首詩,他們好奇的是我為甚麼不把當年的「定稿」寄給「書寫力量」,偏偏選了一首藏在抽屜裏發霉的「初稿」。這當然是「詩人」們的秘密,不可以道破,像洛夫在〈與李賀共飲〉中所說的:「不懂就讓他們去不懂/不懂/為何我們讀後相視大笑」。
(二零一三年六月)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碩士一年級 蔡少鋒
![〈穿過黑夜的大雨回家〉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碩士一年級 蔡少鋒]()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6月 10, 2013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6月 10, 2013
Ra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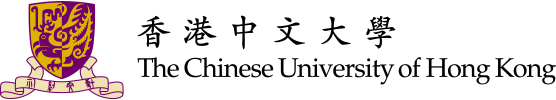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