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正七時醒來,可是天黑得還像五時左右。看了兩個鐘,確是七時。這樣黑,這個山大槪已埋在烏雲裏。窗外落著雨,哪裏是雨,哪裏是雲,很難分淸。不能像毎天似的,走上山頂,迎接新生的太陽,祇有在屋裏徘徊,等著即來的大風雨了。
想起今天沒有甚麼會要開,縱是這樣陰天,心情也比較晴朗些。可是九時要上課,還沒有預備,連一本書昨天也沒有帶回家來。在大雨傾盆中,上了汽車,到科學館祇有幾分鐘的路,到那裏正是八時。還有一小時可以預備功課。
路上想,何必這樣大雨趕去科學館,敎了二十多年書了,也用不著甚麼預備。可是,繼而想,如果不預備一下,因而敎得不夠好時,會因而後悔,痛苦好幾天。
敎書一定不應該是站在那裏對一羣人背一遍書,至少是應像在戲院中對一羣人演一台戲。
可是,早晨九時上台演戲,即使是自己唱作倶佳,觀衆也是在乍醒階段,這台戲也不易唱好啊。我雖然知道十一時開始的課,同樣的東西也要講得精彩些,而課程卻總是排在九時,大概同事們誰也不願太早上課。
傘在車的後面,到了停車坪,雨大得也不能下車,等了幾分鐘,仍是大雨傾盆;祇好下車了。就是到車後拿傘的一段時間,已把全身淋溼,到了辦公室,腳下的溼也覺出來了。
這樣溼的上衣,怎麼穿;不穿西裝上衣上課,對我還是第一次。一小時的預備,當然可以講兩小時,問題是不著戲裝而淸唱,有些不習慣。
課室就在隔壁,我九時十五分正進去的。學生最多祇有七、八個人,到了六分之一,這自然是大雨傾盆路上塞車。我對班上說,我們等半小時以後再說罷。因為今天講相當難的題目,那六分之五的人如不聽講,是不易自己看懂的。
半小時後,人到得差不多了。我講課常從課室中安靜的程度來判斷自己講得好壞。今天講的剛一入題,全課室即非常安靜。外面 的狂風暴雨,我當然聽不見;學生們也聽不見。我講奈奎斯特,好像我自己就是奈奎斯特了,在說自己的心得。正像奥立渥演哈孟雷特,就變成哈孟雷特一樣。這 時,是作演員或作敎師的最大的報酬。正應了中國所說的老話: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時候,在屋中與好幾十個知己西窗剪燭、促膝談心一樣。
這樣,一個半小時,像五分鐘似的過去了。
下課後,回到辦公室,四年級一個作硏究論文的學生在等我,他說,前些日子他做出的一些成果,經我吿訴他再査某一些書以後, 他在驚慌著表示他的結果竟與前人的相類似,所不同者最多祇有半頁。我又得安慰他一番:「你自己創作的結果,竟與前人的相同那麼多,這表示你的聰明才智與那 位前人差不多,即使十分之九是屬於重新發現一次;那十分之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創作了。眞正的貢獻,不會是連篇累牘的,不全是排山倒海的,卻是一 點一點的,一滴一滴的。這樣的貢獻即使是微如毫末,也是了不起的。」他說這幾天連覺也睡不好,腦海中不能驅走所硏究的問題。我說,那表示你要航海,已經上 了船;要遠行,已經上了路了。你現在應該覺得很快樂的;已不計較前人有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他臨離辦公室前,我再囑咐他不知向學生們說過多少遍的老話:「你今年二十一歲了,正是創作的年紀。别忘了牛頓、愛因斯坦, 他們的重要工作都是在二十四以前完成的。」我這種「創作與年輕」的理論,同學們常引為笑談,而這卻是我嚴肅的想法。有一次我在實驗室看他們玩微型電腦,到 了不眠不休的程度,我跟他們說,微型電腦發明人佐伯斯年紀十九歲時就發明了,你們都已經二十歲了,無論如何都太老了,來不及了,今天先回家睡覺吧。
其實,中國的年輕與成就有關的故事更多,以《世說新語》中摯瞻的故事最好玩。在他二十九歲時已有很大成就,王敦說,你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也太早了。瞻說,與你比,也許我早些;與甘羅比, 我已是太老了。
中午,與系裏同事到聯合書院餐廳去吃飯。聯合的飯眞是不錯,但不上山吃飯,已經快半年了。半年前一位同事放例假,沒有他, 中午這個吃飯團就組織不起來。其實他所做的,祇是預先給飯廳打個電話,吃完了他管算帳,毎人分攤多少錢而已,出力也並不多,但沒有他,就大家全不上山。今 天來了五個人,吃了六個菜,其中有肉絲炒豆芽、菜花炒肉片、雞絲炒芹菜,均很可口,毎人攤十一元五角。吃完了,從山上走下,眞是「路轉峯迴出畫塘」,新雨 後的山,特别淸新。回到辦公室還不到一點半。
毎天有一堆信函及文件,面對著這個紙片堆成的小山,就想起《三國》裏的龐士元來。龐士元是把幾個月的文件橫下來一天裏辦 完,我是把一天的文件,祇許自己用兩小時處理。過了兩小時,我就不看了。以不看了之。這樣,雖不至於使自己被文件的洪濤淹沒,或淹死,但,卻苦了秘書,她 又得找東找西,把我不看的,弄出個頭緖來。
今天,有封從美國退回來的論文稿,這是我跳跳躍躍,寫完了,還得意了好幾天的一篇論文,卻退回來了。打開一看,編輯並未轉 給任何人去審查過目,接到以後立時就原封退回。理由是論文的內容太長,頁數過多,要我縮成一半才能繼續考慮。眞是閻王好見,小鬼難搪。傳達室的工役硬是不 給你傳話,你就無從見你想見的人;我旣無時間重寫一遍,也無能力縮成一半,何况,字打得這麼漂亮,重寫,這豈不是白打了。打定主意,原封改寄英國。以頁數 來定取奪,這種以用機械對待創作的方式無異鋼刀對待人,使人無法容忍,也無從容忍。
錢穆的演講是四時十五分開始的,我四時半才想起來。趕去聽錢穆的演講。
錢穆一向是對中國文化抱樂觀的。但一面聽錢的演講時,卻想起一向對中國文化抱悲觀的那位史家—雷海宗。
雷海宗可以說是中國的湯恩比,他是把文化有生有滅那個思想摸式應用於中國歷史。以他的看法,一個文化的興起,是人力所擋不 住的,一個文化的滅亡也是人力所無可挽救的。他以為中國的文化到了五胡亂華時,已經是垮掉了,就像世界上二十幾個文化的興起與垮掉一樣。垮掉了就不會再 興。可是很奇怪,中國文化經過佛敎的衝撃以後,又興起個第二周,從唐又開始了。但到了民國, 這第二周又垮掉了。能不能再起,就不得而知了。這是抗戰時期雷海宗的說法,可以說是很悲觀的,我就是受這種悲觀氣氛的感染,對現時的中國文化一向也未樂觀 過。
可是,最近,因為偶然看到一位畫家的信,使我這一貫悲觀的想法突生改變。這位畫家說,佛敎在隋唐五代的發揚,全國是沸騰到 了家的,可是沸騰的階段過去以後,中國文化又從這種急湍中水落石出的站起來。想一想,十世紀的新宗敎對中國有多大影響,可是卻沒有把中國文化消滅。那麼, 這個二十世紀的新宗敎,把中國帶入了沸騰以後,恐怕也有河淸海平的一天。我卻因為這位畫 家的信心,把自己悲觀的情緖沖淡不少。
我一邊聽錢穆的演講,一邊想起雷海宗及畫家的話,當然並未太仔細去聽。可是,最後,總有個印象,知道他在講甚麼。比起朱光潛那兩天的演講要好多了。因為你在努力聽,也不知朱光潛在講些甚麼。
在大陸的學者,對舉國沸騰的反應是頗不一樣的。比如潘光旦、雷海宗,是屈辱而死;並未改動他們的學說;這是最上乘的反應, 也是最激烈的;比如金岳霖,沸騰時期寫些淸算自己的文字,但印出書來,他自己從前的工作印在前面,而否定自己的文字列為附錄,這樣,我們可以看得淸淸楚 楚,看完了前面,不看附錄就好了。比如沈從文,一九四九年以前寫小說,敎創作;而以後,洗手不寫小說,專搞歷代衣裳服制。而朱光潛則不是;他在沸騰前後, 受苦受難之餘,卻非常用力的硏究起馬克思來。他的新著作裏,遍佈辯證啦、統一啦的字眼,弄得人不易看他的書。我們看不出哪一部分是他自己由衷之言,而又哪 一部分是非說不可的話。難道他不知道,馬克思是一種宗敎,是沒有硏究的餘地的?人家既然說他不配硏究馬克思,他又何必非硏究這樣的題目不可呢?
回到家,大風大雨又作。一晚上,自己的思潮也是大風大雨。想一想錢穆在風雨飄搖之夕,孑然一身南來,還堅持於道統,還盡力於辦學,不能不使人另眼相看。他實在是以身行道,以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在寫一首悲壯的史詩。
但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有一種遺憾的感覺。我給這個時代起了一個名字,叫「無詩的時代」。
錢穆當時的辦學,以及後來的離開香港,是旣悲壯又瀟灑的。可是我們卻看不到他任何心情的有力描述。為甚麼沒有幾首詩留下 來?也許他並不會作詩。錢穆離開新亞書院時,卻引蘇東坡的詩:「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這種句子如果由他自己寫出來,該多悲壯而瀟灑,可惜祇 是引用東坡的。
因為錢穆,又想起新亞另一個創辦人唐君毅,恐怕他也不會作詩罷。於感情宣洩不出來的時候,祇得引用舊詩,或改動舊詩。唐君 毅常給自己像片的題句是:「宇宙無窮願無極,海天遼闊立多時」,這是改用梁啓超的詩;而梁啓超也不太會作詩,而是套用黃仲則的詩。黃的原詩是:「悄立市橋 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
錢穆、唐君毅全不會作詩,更不必說我這一代以及現在正受敎育的一代了。無詩的時代是最可憐的時代,天翻了,地覆了,我們也不能形狀於萬一。
躺在床上,還在想這個無詩的時代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不知甚麼時候卻睡著了。
── 一九八三、四月十日於香港
(網上版: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一年級 張曉瑩同學 校)
想起今天沒有甚麼會要開,縱是這樣陰天,心情也比較晴朗些。可是九時要上課,還沒有預備,連一本書昨天也沒有帶回家來。在大雨傾盆中,上了汽車,到科學館祇有幾分鐘的路,到那裏正是八時。還有一小時可以預備功課。
路上想,何必這樣大雨趕去科學館,敎了二十多年書了,也用不著甚麼預備。可是,繼而想,如果不預備一下,因而敎得不夠好時,會因而後悔,痛苦好幾天。
敎書一定不應該是站在那裏對一羣人背一遍書,至少是應像在戲院中對一羣人演一台戲。
可是,早晨九時上台演戲,即使是自己唱作倶佳,觀衆也是在乍醒階段,這台戲也不易唱好啊。我雖然知道十一時開始的課,同樣的東西也要講得精彩些,而課程卻總是排在九時,大概同事們誰也不願太早上課。
傘在車的後面,到了停車坪,雨大得也不能下車,等了幾分鐘,仍是大雨傾盆;祇好下車了。就是到車後拿傘的一段時間,已把全身淋溼,到了辦公室,腳下的溼也覺出來了。
這樣溼的上衣,怎麼穿;不穿西裝上衣上課,對我還是第一次。一小時的預備,當然可以講兩小時,問題是不著戲裝而淸唱,有些不習慣。
課室就在隔壁,我九時十五分正進去的。學生最多祇有七、八個人,到了六分之一,這自然是大雨傾盆路上塞車。我對班上說,我們等半小時以後再說罷。因為今天講相當難的題目,那六分之五的人如不聽講,是不易自己看懂的。
半小時後,人到得差不多了。我講課常從課室中安靜的程度來判斷自己講得好壞。今天講的剛一入題,全課室即非常安靜。外面 的狂風暴雨,我當然聽不見;學生們也聽不見。我講奈奎斯特,好像我自己就是奈奎斯特了,在說自己的心得。正像奥立渥演哈孟雷特,就變成哈孟雷特一樣。這 時,是作演員或作敎師的最大的報酬。正應了中國所說的老話: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時候,在屋中與好幾十個知己西窗剪燭、促膝談心一樣。
這樣,一個半小時,像五分鐘似的過去了。
下課後,回到辦公室,四年級一個作硏究論文的學生在等我,他說,前些日子他做出的一些成果,經我吿訴他再査某一些書以後, 他在驚慌著表示他的結果竟與前人的相類似,所不同者最多祇有半頁。我又得安慰他一番:「你自己創作的結果,竟與前人的相同那麼多,這表示你的聰明才智與那 位前人差不多,即使十分之九是屬於重新發現一次;那十分之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創作了。眞正的貢獻,不會是連篇累牘的,不全是排山倒海的,卻是一 點一點的,一滴一滴的。這樣的貢獻即使是微如毫末,也是了不起的。」他說這幾天連覺也睡不好,腦海中不能驅走所硏究的問題。我說,那表示你要航海,已經上 了船;要遠行,已經上了路了。你現在應該覺得很快樂的;已不計較前人有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他臨離辦公室前,我再囑咐他不知向學生們說過多少遍的老話:「你今年二十一歲了,正是創作的年紀。别忘了牛頓、愛因斯坦, 他們的重要工作都是在二十四以前完成的。」我這種「創作與年輕」的理論,同學們常引為笑談,而這卻是我嚴肅的想法。有一次我在實驗室看他們玩微型電腦,到 了不眠不休的程度,我跟他們說,微型電腦發明人佐伯斯年紀十九歲時就發明了,你們都已經二十歲了,無論如何都太老了,來不及了,今天先回家睡覺吧。
其實,中國的年輕與成就有關的故事更多,以《世說新語》中摯瞻的故事最好玩。在他二十九歲時已有很大成就,王敦說,你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也太早了。瞻說,與你比,也許我早些;與甘羅比, 我已是太老了。
中午,與系裏同事到聯合書院餐廳去吃飯。聯合的飯眞是不錯,但不上山吃飯,已經快半年了。半年前一位同事放例假,沒有他, 中午這個吃飯團就組織不起來。其實他所做的,祇是預先給飯廳打個電話,吃完了他管算帳,毎人分攤多少錢而已,出力也並不多,但沒有他,就大家全不上山。今 天來了五個人,吃了六個菜,其中有肉絲炒豆芽、菜花炒肉片、雞絲炒芹菜,均很可口,毎人攤十一元五角。吃完了,從山上走下,眞是「路轉峯迴出畫塘」,新雨 後的山,特别淸新。回到辦公室還不到一點半。
毎天有一堆信函及文件,面對著這個紙片堆成的小山,就想起《三國》裏的龐士元來。龐士元是把幾個月的文件橫下來一天裏辦 完,我是把一天的文件,祇許自己用兩小時處理。過了兩小時,我就不看了。以不看了之。這樣,雖不至於使自己被文件的洪濤淹沒,或淹死,但,卻苦了秘書,她 又得找東找西,把我不看的,弄出個頭緖來。
今天,有封從美國退回來的論文稿,這是我跳跳躍躍,寫完了,還得意了好幾天的一篇論文,卻退回來了。打開一看,編輯並未轉 給任何人去審查過目,接到以後立時就原封退回。理由是論文的內容太長,頁數過多,要我縮成一半才能繼續考慮。眞是閻王好見,小鬼難搪。傳達室的工役硬是不 給你傳話,你就無從見你想見的人;我旣無時間重寫一遍,也無能力縮成一半,何况,字打得這麼漂亮,重寫,這豈不是白打了。打定主意,原封改寄英國。以頁數 來定取奪,這種以用機械對待創作的方式無異鋼刀對待人,使人無法容忍,也無從容忍。
錢穆的演講是四時十五分開始的,我四時半才想起來。趕去聽錢穆的演講。
錢穆一向是對中國文化抱樂觀的。但一面聽錢的演講時,卻想起一向對中國文化抱悲觀的那位史家—雷海宗。
雷海宗可以說是中國的湯恩比,他是把文化有生有滅那個思想摸式應用於中國歷史。以他的看法,一個文化的興起,是人力所擋不 住的,一個文化的滅亡也是人力所無可挽救的。他以為中國的文化到了五胡亂華時,已經是垮掉了,就像世界上二十幾個文化的興起與垮掉一樣。垮掉了就不會再 興。可是很奇怪,中國文化經過佛敎的衝撃以後,又興起個第二周,從唐又開始了。但到了民國, 這第二周又垮掉了。能不能再起,就不得而知了。這是抗戰時期雷海宗的說法,可以說是很悲觀的,我就是受這種悲觀氣氛的感染,對現時的中國文化一向也未樂觀 過。
可是,最近,因為偶然看到一位畫家的信,使我這一貫悲觀的想法突生改變。這位畫家說,佛敎在隋唐五代的發揚,全國是沸騰到 了家的,可是沸騰的階段過去以後,中國文化又從這種急湍中水落石出的站起來。想一想,十世紀的新宗敎對中國有多大影響,可是卻沒有把中國文化消滅。那麼, 這個二十世紀的新宗敎,把中國帶入了沸騰以後,恐怕也有河淸海平的一天。我卻因為這位畫 家的信心,把自己悲觀的情緖沖淡不少。
我一邊聽錢穆的演講,一邊想起雷海宗及畫家的話,當然並未太仔細去聽。可是,最後,總有個印象,知道他在講甚麼。比起朱光潛那兩天的演講要好多了。因為你在努力聽,也不知朱光潛在講些甚麼。
在大陸的學者,對舉國沸騰的反應是頗不一樣的。比如潘光旦、雷海宗,是屈辱而死;並未改動他們的學說;這是最上乘的反應, 也是最激烈的;比如金岳霖,沸騰時期寫些淸算自己的文字,但印出書來,他自己從前的工作印在前面,而否定自己的文字列為附錄,這樣,我們可以看得淸淸楚 楚,看完了前面,不看附錄就好了。比如沈從文,一九四九年以前寫小說,敎創作;而以後,洗手不寫小說,專搞歷代衣裳服制。而朱光潛則不是;他在沸騰前後, 受苦受難之餘,卻非常用力的硏究起馬克思來。他的新著作裏,遍佈辯證啦、統一啦的字眼,弄得人不易看他的書。我們看不出哪一部分是他自己由衷之言,而又哪 一部分是非說不可的話。難道他不知道,馬克思是一種宗敎,是沒有硏究的餘地的?人家既然說他不配硏究馬克思,他又何必非硏究這樣的題目不可呢?
回到家,大風大雨又作。一晚上,自己的思潮也是大風大雨。想一想錢穆在風雨飄搖之夕,孑然一身南來,還堅持於道統,還盡力於辦學,不能不使人另眼相看。他實在是以身行道,以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在寫一首悲壯的史詩。
但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有一種遺憾的感覺。我給這個時代起了一個名字,叫「無詩的時代」。
錢穆當時的辦學,以及後來的離開香港,是旣悲壯又瀟灑的。可是我們卻看不到他任何心情的有力描述。為甚麼沒有幾首詩留下 來?也許他並不會作詩。錢穆離開新亞書院時,卻引蘇東坡的詩:「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這種句子如果由他自己寫出來,該多悲壯而瀟灑,可惜祇 是引用東坡的。
因為錢穆,又想起新亞另一個創辦人唐君毅,恐怕他也不會作詩罷。於感情宣洩不出來的時候,祇得引用舊詩,或改動舊詩。唐君 毅常給自己像片的題句是:「宇宙無窮願無極,海天遼闊立多時」,這是改用梁啓超的詩;而梁啓超也不太會作詩,而是套用黃仲則的詩。黃的原詩是:「悄立市橋 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
錢穆、唐君毅全不會作詩,更不必說我這一代以及現在正受敎育的一代了。無詩的時代是最可憐的時代,天翻了,地覆了,我們也不能形狀於萬一。
躺在床上,還在想這個無詩的時代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不知甚麼時候卻睡著了。
── 一九八三、四月十日於香港
(網上版: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一年級 張曉瑩同學 校)
〈四月八日這一天〉 電子學糸老師 陳之藩
![〈四月八日這一天〉 電子學糸老師 陳之藩]()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3月 11, 2013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3月 11, 2013
Ra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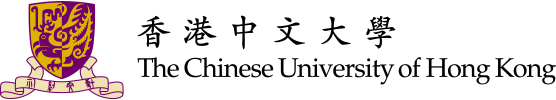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