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感情,隱密幽微,只有自己明白。可寫下來,不意也會引起大大小小許多共鳴。即使不了解,只要寫得美妙,讀著也是賞心樂事一樁。中文系李梓榮同學的〈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student / 記三月二十一日〉,文學指涉豐富,把無以名狀寫得如此繁縟,如此輕盈。
****************************************************************************
近來很惆悵。不是文學手法,也非為字與字間強添一筆沒有底子的感情。自從為書寫力量寫下介紹黑板詩的文章(〈洗手間裡的詩意〉,如果有人在意的話)後,便再也沒有參與書寫力量的活動。這又何苦呢?我質問自己,在刻意逃避了董啟章的講座以後。生活很多問題像一顆顆混圓的黑點,時鐘走了很多里以後才出現隱隱的虛線,略窺無以名狀的情緒。
真的嗎?只需求助於古老的記憶,就可以找到答案?暫時無法解決如此棘手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記憶依附「現在」才能生存。腦袋裡的過去如汪洋深邃,但以河流最幼最多分枝的形態出現。例如,年輕的美,永遠伴隨一種即將毀滅的不安。但只有在成了中年廢物以後,甚麼也成灰成燼了,才能領略年青的美。這,是與現在相對的。普魯斯特活在他的記憶裡嗎?若非父母相繼去世,自己長時間卧病在床,他又有否足夠的興致和魄力去追憶已然逝去的如水年華?
閱讀別人的自傳,常有一種菩薩低眉的不忍卒看之感。讓人(其實只有自己)悲哀的是,自己竟沒有任何值得銘記的失落,日後果真要寫個自傳的話,可能以兩至三筆便能鳴金收兵。Benjamin Franklin 說過either write something worth reading or do something worth writing,抱歉,我們這無所事事的一群活在一個無所事事的年代,寫出的只能是一種無限放大了的鄭重而輕微的騷動。畢竟,甚麼也沒有發生。
三月二十一日,我在讀朱天文。胡蘭成為張愛玲留下的就只是淺淺〈民國女子張愛玲〉一篇。愛情不為甚麼,她為他留下了無數的影子。「胡先生比張愛玲厲害多了」,我很鍾愛的朱天文說。固然這令我很失落,但更令人歎息的是,我只能為別人恩怨情仇而顫動。在這裡,有一種說不出來不能平伏的淒涼。
在九龍塘的Pacific Coffee未搬遷前,經常遇到董啟章。寫東西累了擱筆,遠遠偷偷的觀察他讀書。啊!原來藝術家是如此的。心裡模糊的有個大概,夠了,要聽他/他們的聲音,不敢,亦不想。
在街上,如果你看見我,你會像遇上珍禽異獸般撫摸我,但也許,我會像受驚的野獸,反咬你一口。村上春樹如是說。
****************************************************************************
近來很惆悵。不是文學手法,也非為字與字間強添一筆沒有底子的感情。自從為書寫力量寫下介紹黑板詩的文章(〈洗手間裡的詩意〉,如果有人在意的話)後,便再也沒有參與書寫力量的活動。這又何苦呢?我質問自己,在刻意逃避了董啟章的講座以後。生活很多問題像一顆顆混圓的黑點,時鐘走了很多里以後才出現隱隱的虛線,略窺無以名狀的情緒。
真的嗎?只需求助於古老的記憶,就可以找到答案?暫時無法解決如此棘手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記憶依附「現在」才能生存。腦袋裡的過去如汪洋深邃,但以河流最幼最多分枝的形態出現。例如,年輕的美,永遠伴隨一種即將毀滅的不安。但只有在成了中年廢物以後,甚麼也成灰成燼了,才能領略年青的美。這,是與現在相對的。普魯斯特活在他的記憶裡嗎?若非父母相繼去世,自己長時間卧病在床,他又有否足夠的興致和魄力去追憶已然逝去的如水年華?
閱讀別人的自傳,常有一種菩薩低眉的不忍卒看之感。讓人(其實只有自己)悲哀的是,自己竟沒有任何值得銘記的失落,日後果真要寫個自傳的話,可能以兩至三筆便能鳴金收兵。Benjamin Franklin 說過either write something worth reading or do something worth writing,抱歉,我們這無所事事的一群活在一個無所事事的年代,寫出的只能是一種無限放大了的鄭重而輕微的騷動。畢竟,甚麼也沒有發生。
三月二十一日,我在讀朱天文。胡蘭成為張愛玲留下的就只是淺淺〈民國女子張愛玲〉一篇。愛情不為甚麼,她為他留下了無數的影子。「胡先生比張愛玲厲害多了」,我很鍾愛的朱天文說。固然這令我很失落,但更令人歎息的是,我只能為別人恩怨情仇而顫動。在這裡,有一種說不出來不能平伏的淒涼。
在九龍塘的Pacific Coffee未搬遷前,經常遇到董啟章。寫東西累了擱筆,遠遠偷偷的觀察他讀書。啊!原來藝術家是如此的。心裡模糊的有個大概,夠了,要聽他/他們的聲音,不敢,亦不想。
在街上,如果你看見我,你會像遇上珍禽異獸般撫摸我,但也許,我會像受驚的野獸,反咬你一口。村上春樹如是說。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student / 記三月二十一日〉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二年級 李梓榮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student / 記三月二十一日〉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二年級 李梓榮]()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5月 20, 2013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5月 20, 2013
Ra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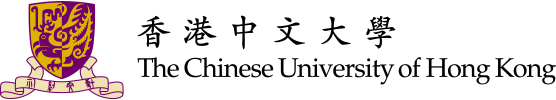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