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孕育了不少文人,許多文人也寫過這山城與海港。邱嘉耀同學的這篇〈中大文學散步後記〉本身也是一篇寫得極好的散文,而且問題問得極好:「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自然定必讓步於經濟,為家園奮鬥竟變質為『不顧大局』?」)
****************************************************************************
學期尾聲,原來我已在中文大學快將待了一個年頭了。兩個學期以來,還沒有遊遍中大,至於認認真真的細賞,更加談不上。適逢葉老師邀我任學生助理,帶領一批中學生,才得真正放慢步伐,緩緩地走一趟。
是日天氣頗佳。天氣好與不好,不在於天空清朗明麗,也不在於雲朵聚合流散,而是相對的。昨天中午起便下起滂沱大雨,淅淅瀝瀝, 夜半還隱隱透著雨打窗門的聲音。這是暮春的雨吧?春雨綿綿使人愁,行人不但狼狽,春風挾著雨水所帶來的寒意,更是亂人心神。今天舉頭一望,清曠固是難見, 疏朗亦不可向邇,遠遠望去,一幅半灰半白的霧氣漫滿天際,柔柔的陽光從中滲透出來。「天朗氣清」是旅遊的佳日,但佳日不可奢求;雷公不鳴,雨師不奏,便足 以令人心滿意足了。
幸好風伯眷顧我們。輕輕的涼風隨著葉老師自迷你擴音器響起的聲音吹來,令一眾師生抖擻不少。我們翻著余光中的〈春來半島〉,先 在百萬大道重踏詩人的足跡。可惜花時已過,只零星掛著如荷蘭豆──但又比荷蘭豆更扁更長──的莢果;若要從枝椏間覓得未凋的花朵,則極為難得。看不到「花 開五瓣,嫩蕊纖長」而作淡玫紅色的宮粉羊蹄甲,只好仰視那雙瓣分岔的綠葉,從那零落的綠色裡,想像一下花潮般的燦錦爛繡。
紅花杳杳,松杉卻聳然矗立。邵逸夫夫人堂的階前立著一整排松杉,縱是植於坡上,仍不減其峨巍之姿。余光中寫道:
挺立的蒼榦,疎疎的翠柯,卻披上其密如繡其虛如煙的千億針葉,無論是近仰遠觀,久了,就會有那麼一點禪意。
確是傳神。尤其是那密密的松針,有花針之嬌柔纖細,卻無金屬冰冷刺人之感。此時不禁神馳八荒,倘若勁風驟起,針葉緩緩飄落,細 葉觸面,應如玉指輕拂,而一身滿是綠意,又是何其浪漫!我不知道松針會否如蒲公英、楊柳那樣輕易便抛家傍路,其榦如許筆挺,其葉又如許低柔,剛柔都集於一 身,實在難以判斷。此時,葉老師正說到松濤,著同學感受一下。同學一聽:葉落無聲,沒有;葉擺風輕,也沒有。只見一人指向何善衡工程大樓,說:「我只是聽 到發電機的聲音。」我們只好又幻想,幻想夜半闃寂無人時劃破凝靜的空氣的不是機器,而是風過處隱隱起伏的松濤。
這次終究是導賞團,並非教人神遊天外攫取靈感的冥想之旅。自李兆基樓三樓天橋出去,便見最使詩人難忘的相思樹。天橋右首的台灣相思,確有如噴如爆之勢,花葉一併向小橋探來,其生意之盎然,較之「一枝紅杏出牆來」,後者未免太落寞、太孤單了。
沿著近欄杆的行人道走,便見吐露港。海上蒙上一陣薄霧,灰灰的使人看不真切,平日的碧波萬頃、千畝藍田也大大失色。海上還佈置 著工作台和吊臂,春色三分,暮春帶去一分,天公不造美,又減去一分,連僅餘的春色也被那無情的鋼鐵奪走了。興味難免索然。此時正讀到王良和的〈吐露港填 海〉,方知吐露港在二十年多年前填過一次,以無情的泥沙掩蓋大學火車站毗連的大海。廿年後的今日,政府又蠢蠢欲動,醞釀著一個災難。葉老師問同學有何看 法,說到有人贊成填海,卻竟以「填海後可徒步到達彼方,方便至極」為由。如何不使人無奈呢?我看著海,有人卻驚異於雨後出來的溝渠裡的長長蚯蚓。一聲尖 叫,把許多同學的目光吸引過去。也許,生活亦是如此。
踏著碎碎的步,我們遙觀了聯合、新亞的兩座水塔,又拜訪了孔子與唐君毅,在天人合一亭附近拍下一幀合照,導賞團便告解散。
我回到宿舍後,仍然想著昔日那千頃萬頃的海灣。我驟然想起數日前一個朋友問我:「你知道新亞將來建的新宿舍可能會遮擋水塔嗎? 你有什麼看法?」我登時愣了一愣,說不出話來。心中暗忖:「新亞向來被詬宿位匱乏,新建宿舍,的確方便不少學子;但,景觀遭到破壞,總是不好。」平衡兩 方,我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只好含糊道:「政府不是被人說扣留不少土地儲備嗎?」朋友似乎沒有留意到我言辭的不著邊際,說:「有人訾議中大師生因填海 『填在我的後花園』而反對,論點實在站不住腳。」我又愣住了。朋友迸出一句,如晴天霹靂:「難道不可以為保護我們的校園而反對嗎?」
是啊!難道我們不可以為保護我們的校園而反對嗎?這麼直截了當的理由,我竟然想不到!為了建三峽大壩,淹沒了多少座城,湮滅了 多少人的家鄉?為了推廣雲南的旅遊業,破壞了多少風貌,趕絕了多少原居民?難道我們不可以「保衛家園」為由,對抗無理的入侵?難道除了填海一途,便別無他 法?為何二十年後的今天又再奪走那幾不成海的海,為何要破碎一眾師生在二十年後的回憶?
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自然定必讓步於經濟,為家園奮鬥竟變質為「不顧大局」?
我看看書桌上的文字,再看看窗外的吐露港,突然感到有一點陌生──那已是歷史,已成陳跡。
****************************************************************************
學期尾聲,原來我已在中文大學快將待了一個年頭了。兩個學期以來,還沒有遊遍中大,至於認認真真的細賞,更加談不上。適逢葉老師邀我任學生助理,帶領一批中學生,才得真正放慢步伐,緩緩地走一趟。
是日天氣頗佳。天氣好與不好,不在於天空清朗明麗,也不在於雲朵聚合流散,而是相對的。昨天中午起便下起滂沱大雨,淅淅瀝瀝, 夜半還隱隱透著雨打窗門的聲音。這是暮春的雨吧?春雨綿綿使人愁,行人不但狼狽,春風挾著雨水所帶來的寒意,更是亂人心神。今天舉頭一望,清曠固是難見, 疏朗亦不可向邇,遠遠望去,一幅半灰半白的霧氣漫滿天際,柔柔的陽光從中滲透出來。「天朗氣清」是旅遊的佳日,但佳日不可奢求;雷公不鳴,雨師不奏,便足 以令人心滿意足了。
幸好風伯眷顧我們。輕輕的涼風隨著葉老師自迷你擴音器響起的聲音吹來,令一眾師生抖擻不少。我們翻著余光中的〈春來半島〉,先 在百萬大道重踏詩人的足跡。可惜花時已過,只零星掛著如荷蘭豆──但又比荷蘭豆更扁更長──的莢果;若要從枝椏間覓得未凋的花朵,則極為難得。看不到「花 開五瓣,嫩蕊纖長」而作淡玫紅色的宮粉羊蹄甲,只好仰視那雙瓣分岔的綠葉,從那零落的綠色裡,想像一下花潮般的燦錦爛繡。
紅花杳杳,松杉卻聳然矗立。邵逸夫夫人堂的階前立著一整排松杉,縱是植於坡上,仍不減其峨巍之姿。余光中寫道:
挺立的蒼榦,疎疎的翠柯,卻披上其密如繡其虛如煙的千億針葉,無論是近仰遠觀,久了,就會有那麼一點禪意。
確是傳神。尤其是那密密的松針,有花針之嬌柔纖細,卻無金屬冰冷刺人之感。此時不禁神馳八荒,倘若勁風驟起,針葉緩緩飄落,細 葉觸面,應如玉指輕拂,而一身滿是綠意,又是何其浪漫!我不知道松針會否如蒲公英、楊柳那樣輕易便抛家傍路,其榦如許筆挺,其葉又如許低柔,剛柔都集於一 身,實在難以判斷。此時,葉老師正說到松濤,著同學感受一下。同學一聽:葉落無聲,沒有;葉擺風輕,也沒有。只見一人指向何善衡工程大樓,說:「我只是聽 到發電機的聲音。」我們只好又幻想,幻想夜半闃寂無人時劃破凝靜的空氣的不是機器,而是風過處隱隱起伏的松濤。
這次終究是導賞團,並非教人神遊天外攫取靈感的冥想之旅。自李兆基樓三樓天橋出去,便見最使詩人難忘的相思樹。天橋右首的台灣相思,確有如噴如爆之勢,花葉一併向小橋探來,其生意之盎然,較之「一枝紅杏出牆來」,後者未免太落寞、太孤單了。
沿著近欄杆的行人道走,便見吐露港。海上蒙上一陣薄霧,灰灰的使人看不真切,平日的碧波萬頃、千畝藍田也大大失色。海上還佈置 著工作台和吊臂,春色三分,暮春帶去一分,天公不造美,又減去一分,連僅餘的春色也被那無情的鋼鐵奪走了。興味難免索然。此時正讀到王良和的〈吐露港填 海〉,方知吐露港在二十年多年前填過一次,以無情的泥沙掩蓋大學火車站毗連的大海。廿年後的今日,政府又蠢蠢欲動,醞釀著一個災難。葉老師問同學有何看 法,說到有人贊成填海,卻竟以「填海後可徒步到達彼方,方便至極」為由。如何不使人無奈呢?我看著海,有人卻驚異於雨後出來的溝渠裡的長長蚯蚓。一聲尖 叫,把許多同學的目光吸引過去。也許,生活亦是如此。
踏著碎碎的步,我們遙觀了聯合、新亞的兩座水塔,又拜訪了孔子與唐君毅,在天人合一亭附近拍下一幀合照,導賞團便告解散。
我回到宿舍後,仍然想著昔日那千頃萬頃的海灣。我驟然想起數日前一個朋友問我:「你知道新亞將來建的新宿舍可能會遮擋水塔嗎? 你有什麼看法?」我登時愣了一愣,說不出話來。心中暗忖:「新亞向來被詬宿位匱乏,新建宿舍,的確方便不少學子;但,景觀遭到破壞,總是不好。」平衡兩 方,我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只好含糊道:「政府不是被人說扣留不少土地儲備嗎?」朋友似乎沒有留意到我言辭的不著邊際,說:「有人訾議中大師生因填海 『填在我的後花園』而反對,論點實在站不住腳。」我又愣住了。朋友迸出一句,如晴天霹靂:「難道不可以為保護我們的校園而反對嗎?」
是啊!難道我們不可以為保護我們的校園而反對嗎?這麼直截了當的理由,我竟然想不到!為了建三峽大壩,淹沒了多少座城,湮滅了 多少人的家鄉?為了推廣雲南的旅遊業,破壞了多少風貌,趕絕了多少原居民?難道我們不可以「保衛家園」為由,對抗無理的入侵?難道除了填海一途,便別無他 法?為何二十年後的今天又再奪走那幾不成海的海,為何要破碎一眾師生在二十年後的回憶?
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自然定必讓步於經濟,為家園奮鬥竟變質為「不顧大局」?
我看看書桌上的文字,再看看窗外的吐露港,突然感到有一點陌生──那已是歷史,已成陳跡。
〈中大文學散步後記〉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一年級 邱嘉耀
![〈中大文學散步後記〉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一年級 邱嘉耀]()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5月 13, 2013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5月 13, 2013
Ra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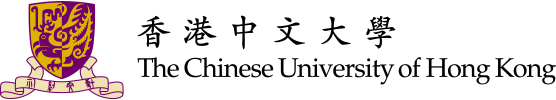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