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海明威,不是虎師
歲月安穩靜好,日日海樓見翠微。今天早上有陽光,步出家門,帶兒子到培道中學氹仔小學部,然後自己乘短程校車到澳門大學中文系訪問教授辦公室。從「家」到「室」,一共用了25分鐘──每天一個精算師般的精準數字。辦公即教學、研究、寫作。中午簡單進食,傍晚飯菜稍豐。
3月21日,就如年來很多個日子一樣,有什麼好記的呢?「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瘂弦的詩〈如歌的行板〉如是說。我非海明威,也非魯迅、胡適;3月21日的記事,將來不可能成為研究的對象。魯迅上海時期的日記,缺了好幾天,胡菊人為此大做文章,有頗驚人的發現。胡適美國時期的日記,有好些女性名字,一位歷史學家憑此考證出,北大校長令某些人羨慕的風流倜儻。
安穩地打開電腦,看「易妙」,看新聞,整理一下講義,必要時重溫一下講授要點,與同室的另一位訪問教授離開辦公室上課去了。室友商金林教授來自北京大學中文系,與我的上課時間一樣,我們同步同路,一起去「勞動」。勞動是我的用語,他欣然沿用。
上午這一科「文學理論」是學年課程,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都要講。今天概述20世紀中華文學理論家及其理論,其中有梁實秋。他反浪漫、倡古典、持普通人性說、與魯迅激烈論爭,都講了。班上六十多人,都是大四學生,選修的科目多,加上正在撰寫畢業論文,正在作就業和深造的準備,加上可能早一個晚上沉醉於智能手機的繽繽紛紛而不能自己,不是人人都精神奕奕,專心聆聽以枯燥見稱的文學理論的。我於是加插了一小段反浪漫主義者梁實秋悼亡之後的浪漫忘年黃昏之戀。澳門大學的學生有本澳的,也有內地的,中文系的女生多於男生。我又講了歐陽子、龍應台、陳幸蕙幾位台灣女性批評家的貢獻。幾個內地背景的學生似乎對她們表示了較多的興趣。
我向學生預告,以後講的重點將是王國維和錢鍾書。錢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說與梁實秋的「普通人性」說,互相發明。中華知識分子之深識西方文化者,大概都持梁、錢之說,否則反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名過其實,我常為眾多學者的褒貶任聲而嘆息。我要求學生閱讀《從文心雕龍到人間詞話》一書,這是拙著《中國古典文論新探》的增訂版,今年一月才面世的。
老師叮嚀學生看書,學生是否聽話,真難說;我不是Tiger Teacher,從不作虎嘯,更無獅吼。這裏忽然來了個「虎師」,有分教,因為中午我將提及Tiger Mother一詞。雖然難以達標,「樑師」力求成為良師,而非虎師;我在香港、美國、內地、台灣,目前在澳門教書,都如此。
在香港中文大學當過四年學生,當過二十四年的講師、高級講師、教授;離開中大十二年了,卻依然有不少聯繫。中大新亞書院與美國耶魯大學有二校學生交流活動。近日幾個耶魯的學生到了香港參觀訪問,順便來澳門,今天在澳門半島有一午餐會。當年我在新亞書院擔任過通識課程主任、輔導長、《新亞生活》主編、署理院長等職,曾參與YUNA(耶魯大學、新亞)交流活動的創辦。新亞書院院務室的霍偉基兄知我人在澳門,盛情邀請我這個舊新亞人參加午餐會。
新亞、雅禮、金耀基
上午的課下了,我打的「飛車」從氹仔的澳門大學出發赴會。「十六浦」的海風(Mistral)餐廳長桌排排坐了連我在內的十六人:七位耶魯同學、六位新亞同學、新亞校友「自由藝術家」(free-lance artist)黃小姐、偉基兄和我。我們沒有「浦」酒吧,當然更沒有「浦」娛樂場所,只是文雅有禮地交談。Yale譯為雅禮,大概是新亞書院創辦人錢賓四夫子的得意之作,雅禮之譯雅於耶魯。我們雅禮地交談,並舉杯慶祝YUNA二十周年。偉基兄洋名Nixon。他告訴我,是次索菲特酒店因為預訂的普通客房客滿了,乃讓他們升級住進總統套房。聽聞這一好消息,我馬上向尼克松總統(President Nixon)恭喜。Nixon是這個YUNA交流活動的執行者,他見多識廣,辦事認真妥善,我對這位舊同事一向讚譽有加。
我與眾人交談時,戲稱耶魯七位同學為耶魯七賢Seven Sages from Yale,用的是竹林七賢的典故。問答間,知道他們中沒有人主修中文,於是補充說:七者,七大奇觀、七大支柱、7-UP也,七者吉也,希望他們不會聯想到七個小矮人。耶魯七賢出乎意料地文靜,我主動出提出問題:貴校的法律系教授,那位寫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虎媽戰歌》)的,你們認識嗎?虎媽無犬女,她的女兒都在名校讀書;你們的媽媽也是虎媽嗎?你們知道1970年代的賣座電影《愛情故事》(Love Story)的原著作者Erich Segal曾是貴校的教授嗎?
我也自問自答了一椿往事。當年中大的校長是光纖之父高錕教授,在甄選新亞同學前赴耶魯交流時,我問過某申請者一個問題:「中大的校長是誰?」該生竟然答不出來。耶魯七賢中的一個問我:「這個學生的申請成功嗎?」我說:「我記得的是:該生沒有到美國訪問貴校的好運氣。」我並補充說:高錕先生當年是貝爾實驗室(Bell Lab)的首席科學家,也是耶魯的兼任教授(adjunct professor)。
說的「當年」太多了,耶魯七賢和同座的新亞六賢一定對我這個「老餅」老師不耐煩了。話題轉換,美食繼續,十六人其喜洋洋。我下午還有課,只得早退,「飛車」回澳大。途中我繼續懷舊,想起新亞雲起軒的晚餐聚談。如有新亞院長金耀基教授在場,不論他任主持、主講,或只是作一發言,必令出席者口福之餘還飽耳福;機智風趣、開胃解頤是金公金口一開的金牌風格。金院長(後來是中大校長) 對劍橋大學的書院制度體會深刻,所撰《劍橋語絲》諸篇散文,叙事、寫景、抒情、議論,筆調靈動多姿,還融匯了劍橋大學的正史、逸聞,為寫劍橋諸名家中我最愛讀的。懷舊?沙田校園可懷者真多,如如魚得水的「余群」。啊,「那些年」、「那些逝去的日子」! Those were the Days,瑪麗.霍普金(Mary Hopkin) 的,那些年,我那一輩的大學新鮮人,唱到現在的華年老教授。
杜甫:但恐誅求(需索)不改轍
下午的課是「古典文學專題:杜甫詩」,今天講的是〈枯棕〉、〈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釋悶〉、〈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這幾首。它們並不在我重點講解的範圍內,但「杜甫出品,必屬佳作」,幾可斷言。棕櫚樹有毛,割剝下來可製繩索等物。「其皮割剝甚,雖眾亦易朽」;杜甫寫枯朽的棕櫚,其實針對的是剝削百姓的官吏,他為此「沉嘆久」。杜甫嘆啊,悶啊,擔心向百姓需索無道的官吏不能改邪歸正,即〈釋悶〉說的「但恐誅求(需索)不改轍」。眼前當政者說「腐敗與政府的性質水火不相容」,杜甫一千多年前已大聲疾呼。詩聖要「正乾坤」但「無力」,希望目前的為政者有力,且有大力。
耕田的鄉親父老為什麼邀請杜甫暢談暢飲以至泥醉,且盛讚嚴中丞嚴武?只不過因為杜甫的上司嚴武推行了惠民的德政。〈泥飲〉這首詩沒有「語不驚人死不休」那類警句,但人物極其生動、風趣,與其主流的沉鬱格調明顯不同。
〈丹青引〉的名句多,至今流傳的「文采風流」、「別開生面」、「英姿颯爽」、「慘澹經營」……以至「寫真」等,是一大筆文學遺產。曹霸獲邀至長安興慶宮的南薰殿繪畫唐朝功臣,好比文藝復興時期米開朗基羅被教皇聘去梵蒂岡的西斯廷教堂,繪畫《聖經‧創世記》的故事。曹霸畫馬更是一絕,下筆神速,「一洗萬古凡馬空」。班上的學生都是大四的,都上過上午「文學理論」的課。他們靜靜地聽著,頗為專注。我說:「新批評學派強調反諷(irony)的意義。在這首〈丹青引〉中,開篇杜甫說畫家本為魏文帝曹操的後裔,而今被貶為庶民;結尾則謂『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潦倒如此,而名為『霸』,真是一大反諷!」我還舉出一些古今作品,說明名實相乖的諷刺。
杜甫後半生的詩,多的是詠嘆調,個人、時局、諸多認識的藝術家,都引生出一曲曲的沉鬱調子。杜甫寫曹霸、公孫大娘、李龜年,都寓有對自己的感慨。〈丹青引〉中我特別喜歡「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這兩句。想來同鄉陳少華兄也喜歡,近年他有散文集以這七個字為書名,刻畫其心境。講解〈丹青引〉之際,接到一個電話。「不知老將至」?消息傳來,興起了一陣生老病死的悲哀。
筆鍵不知老將至
杜甫「下課」,我回到辦公室繼續勞動。有三十餘年歷史的澳門大學,校舍依山坡而建,樓宇支柱是現代吊腳樓的腳,樓宇間相連的走廊是現代的棧道。近萬個學生的校園,是丘陵上小巧的山莊;今年暑假澳大搬到珠海市的橫琴島,將是一片平原上大度的華樓,新校園面積是目前校園的二十倍。我轉樓層穿甬道,抵達小室,打開電腦,澳大網頁上出現新校園工程進展的最新照片。大概每隔一周或一旬,就有「捷報」。圖書館大樓位於校園前端的中央,最為壯麗。館長潘華棟博士,是新亞校友,也是新亞錢穆圖書館的前任館長。他和同事們屢月經年在籌備今年夏季的「大清貨」、「大搬遷」。我曾有嵌名聯贈這位館長:「華夏喜迎四海客,棟樑充滿五洲書」。目前他大忙,我不敢打擾。
2012年8月來澳大中文系任教,之前好幾年在台灣佛光大學。我本來是電腦盲,佛光的歲月為我啟蒙開光;操作電腦文書的基本功,我具備了。「小蒙恬」手寫板助我啟蒙居功甚偉。我或用筆手寫,或按鍵輸入,百度或谷歌的億萬條資料,都可尋搜,又「易」又「妙」(「易妙」是我對email 的翻譯)。我現在備課、做研究、寫文章,都離不開電腦,一筆筆,一鍵鍵,總是一篇文章未完成,一篇文章又在醞釀,一筆筆,一鍵鍵。也有完全舊式手工業的:用普通的紙筆寫下文章,把手稿寄給或傳給報刊的編輯,由他們為我打字。
一篇篇文章發表,一本本書出版。想起杜甫的「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管他名著不著,管他人老不老。丹青不知老將至、筆鍵不知老將至!內子說文章寫得四平八穩,名聲就不會響亮。她這句話有局部的真理。近年我修理過馬大爺和顧教授,但我不會說:要傳揚中國文化的話,一個章子怡抵得過一萬個孔夫子;我不會說:某個城市的人是某種動物。歲月安穩,我的文章也安穩。今天下午繼續從事腦力勞動。也許,五月赴北京和呼和浩特演講,我可呼號這樣的觀點:中華很多學者都是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的「後學」,崇洋過了頭;其實,中國古代文論是織錦,引進的西方20世紀文論是錦上所添之花而已。我依然要求自己立論平正穩當,希望有君子之風,或者如朱壽桐說的,有新月派胡適、徐志摩那種紳士風範。
母鹿柔順,陽光金黃
一周只有周一和周四兩天有課,但我天天上班,幾乎都是朝九晚五,甚至更早到更遲退。我對商教授戲稱敝室二人為「勞模」,他並不婉拒此殊榮。關於勞動,我有打油詩曰:「勞動復勞動,勞動何其多;引頸待周末,海靜樹扶疏。」其實到了周末,一樣有筆有鍵的勞動;勞動是神聖的,我應為勞動寫一首加油詩才對。衡兒五點鐘放學,我同時下班。家在Edificio Hung Fat。Edificio者葡萄牙文大廈、樓宇之意也。活到老,學到老。幾個月來,我先學會了然後教會了衡兒一些葡文單詞; Edificio是何義、怎樣讀, Ponte 16(十六浦)的ponte是何義、怎樣讀,衡兒既被教,則學之;不過他對電視的動畫興趣更大。他和他媽媽都知道我愛看電視新聞,而傍晚時間家中誰的選台權大,不無爭議。我往往慨嘆父權、夫權的旁落。
不過,今天我和平地奪了權。六點鐘了,我選按了「本港台」,等待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鏡頭出現。我打算陪他出訪的彭麗媛也出現時,就第一時間叫內子從廚房走來廳堂,看看第一夫人穿的是什麼服裝。萬眾矚目於雅麗的夫人,大家都會對她評頭品服。我先鋒地看「新聞提要」,沒有習主席,當然也沒有彭女士的消息,再看也沒有。原來我弄錯了日子,他們要到明天才離京出訪。
內子名婕,婕者潔也、捷也;家居潔,家務捷。我已寫過文章述其潔與捷。下午五時半開始預備晚飯,晚飯幾乎頓頓食有魚。衡兒嗜肉嗜魚,嗜魚多於一切食物;他愛吃皮,特別是魚皮。我的外祖父打魚為生,媽媽吃魚長大,我和兄弟姐妹都愛吃魚。魚是吾家食。黃若衡這名字多年前差一點變成「黃金周」(預產期正當五一黃金周)。現在可多來個小名,稱為黃魚皮,簡稱黃皮,怎樣?黃皮可是一種水果,它有金黃色的皮,營養頗豐富。今天晚上的魚是䱽魚──蒸䱽魚。
去年秋天王蒙到澳大訪問,擔任一個月的「駐校作家」。衡兒幸運,一個月內多次與王蒙爺爺見面、合照。王蒙說過多次,學習是他的硬道理、硬骨頭。 我深然其說,並以之教子。吃飯時恐怕一旦我教導他學習,魚的軟骨或硬剌會傷及喉嚨,於是暫時不行「王道」。吃完了,我問衡兒今天在學校學了什麼,他只提到學唱歌,學的是Doe,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原來老師教他們這班小一學生電影《仙樂飄飄處聞》(The Sound of Music)的一首著名插曲〈Doe, ray, me〉。我喜愛此曲,會唱此曲,於是父子合唱,內子和聲伴唱。母鹿柔順,陽光金黃,自我開懷……音樂之聲真善美。台灣把片名譯成〈真善美〉。
文采風流「都瑞美」
晚飯後三人或勞或逸,各有活動。在澳門,我們可收看本澳、香港、大陸、台灣四地數十個電視台。四地我都關心,城事、國事、天下事我如果事事關心,光是新聞節目就可以消耗我逾百分鐘的時間。在深圳看翡翠台和本港台的新聞報告,一遇到「敏感」事件,就有監督部門用迅雷掩目,以極速遮蓋了畫面。在澳門沒有這樣的查禁,心境為之寬暢:暢所欲看。但我不能多看電視,而要常看書、常寫字。我慶幸在香港在深圳在宜蘭在澳門,總有一張或大或小的書桌,靜靜地,供我讀書寫作。眼倦手倦的時候,又有綠色的樹或藍色的海,讓我養眼舒心。
Edificio Hung Fat我們住所有大窗面向海域,及其北的澳門半島;視野宏闊,山、海、樓、樹,日夜色相不同,卻都像范仲淹說的「春和景明」。夜色璀璨,流光溢彩,主要來自博彩。澳門的博彩業收益,數年前已超過美國的拉斯維加斯。拉城有內華達大學,澳門有澳門大學。澳大的經費相當一部份來自博彩業收益。博彩業的龍頭大哥是「威尼斯人」,「威尼斯人」所賺的錢,會培養出「翡冷翠人」?但丁和達芬奇都是「翡冷翠人」。
妻子和兒子在家常活動後都睡了,我仍據書桌在燈下勞動,一筆筆或一鍵鍵的操作。丹青不知老將至,筆鍵不知老將至。筆「健」不知老將至?仍要寫一篇3月21日的日記。數十年前有《中國的一日》,後來有《中大的一日》,現在則有《廿一世紀中大的一日》。為什麼定為3月21日?上個月沒有問及選此日子的原因,就答應善標寫了。 寫這天的日記,用什麼題目好呢?就改動杜詩的二字,用「筆鍵不知老將至」吧。「丹青不知老將至」的下面是「富貴於我如浮雲」,這一句也適合為我座右。〈丹青引〉的「文采風流今尚存」一句也非常好,無論時代環境如何科學、如何商業或者如何博彩,我們特別是凡我文學之輩仍然要存文采,要傳文采。三十年前中大校園就綻開過文采風流的一個小盛唐,思果、余光中、梁錫華、黃國彬等「余群」,都是或應是名垂漢語新文學史的。可是,杜甫「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我們來唱詩歌吧,最好也與妻兒同唱:3月21日,3─2─1,1─2─3,Doe─Ray─Me,唱一首「都瑞美」!
【補記】上面的記事提到3月21日下午接到一個電話,那是胡志偉兄打來的,說何沛雄教授過世了。是日和此後數天我上網或閱報瀏覽,都沒有發現相關的訃聞。25日在《大公報‧大公園》讀到曾敏之先生的詩〈深切哀悼何沛雄教授〉,寫作的日期是3月20日。這首七律的末聯是「平生不負縹湘志,著述三都溉士林」,稱其舊體文學的成就。這使我想起中大的舊同事、前輩蘇公文擢教授。我論香港文學,新詩、舊體兼顧。另一位舊同事黃坤堯教授對香港的舊體文學研究下過深功夫。蘇、何以及目前身健筆健的陳耀南、黃坤堯,當然還有曾公本人,都寫過很多為時為事的詩詞佳作,為香港文學撰史者,不能忽略。曾老已屆九十六高齡,寶筆仍暢達有力,令人欽敬。
*作者曾在本校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任教(1976-2000年),目前是澳門大學中文系客席教授。
〈唱一首「都瑞美」〉 新亞中文系1969年畢業 黃維樑
![〈唱一首「都瑞美」〉 新亞中文系1969年畢業 黃維樑]()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4月 24, 2013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4月 24, 2013
Ra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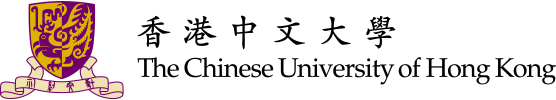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