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一九八三年,我差一點把香港中文大學的「四月八日」給忘了。三十年後,二零一三年的「三月二十一日」,我卻把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記得清清楚楚。
這天中午,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黃懿慧教授要在政大傳播學院的「傳播沙龍」上分享研究心得。黃教授是位教學與研究兼優的年輕「老」友,曾在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告系任教,五年半前,中大把她「挖」走了。說來真巧,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九一年,我曾在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前身「新聞與傳播學系」服務十六年之久,如今,兩人對調,她去了中大,我則回到了政大,我的母校。
三十年前,我距不惑之年還差一小截,孩子們常常在中大校園和同事的孩子跑來跑去,並且一起參加在邵逸夫堂舉辦的「兒童才藝表演」。三十年後,「今不稀的七十」已熱情地向我招手,當年猶是小孩的子女也都成家並且有了小孩,老大雖然仍在中大跑上跑下,但身分已從「眷屬」變成了「教職員」,由校園「跑」進了辦公室。三十年前的「四月八日」,我在吐露港旁的人文館與新傳系姚霞及張結鳳指導她們的學士論文,三十年後的「三月二十一日」,我則在台北木柵景美溪旁的政大研究大樓討論論文,進進出出的有新聞系的博士生熊培伶、東亞研究所的碩士生莊欣怡和亞太研究所的捷克碩士生Jan Meissler。三十年前,我在中大指導學生,那是我的職責,三十年後,我自政大「退而未休」,指導學生成了我的樂趣。三十年前的那篇文章是用手寫的,三十年後的這篇文章則是用電腦打出來的。時代變了,科技變了,有沒有沒變的東西呢?
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我忘了去聽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教授的公開演講:〈中國文化演進的幾個階程〉,也沒記得去聽社會系鄺振權老師在新亞書院雙週會講〈微型電腦對社會的影響〉。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初,個人電腦方才面市不久,我要到一九八六年下旬才買了一台386型的桌上電腦,當時這已是新科技,運算功能也頗強大,但從今天的標準看,速度奇慢,記憶體更微不足道。那時擁有個人電腦的人不多,用的是5 x 5的軟碟,以及後來出現的3 x 3硬碟。三十年後,電腦的能量、普及度與影響恐怕是三十年前無法想像的,手提電腦、手機、平板(iPad)電腦早已進入尋常百姓家,記憶體更不知要大過當時多少倍,20G或40G,甚至60G都已不稀罕,儲存量小得可憐的軟碟、硬碟早成了歷史名詞和博物館的收藏品,取而代之的是16G、32G或64G的隨身碟,行動硬碟的記憶卡容量更可高達1T或2T。三十年前,桌上電腦應屬令人稱羨的「時髦」玩意,如今則問津者日稀,有興趣的用家似乎大多是專業人士,完全被超輕薄的平板、筆記本電腦或手機取而代之的日子看來也已為時不遠。
聽說,新傳學院的老友正在替香港規劃一個新聞傳播博物館,這實在是個留住傳播科技記憶的好主意。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我仍在台灣讀大學,只曉得電腦是新科技,那時旅美數學家林二博士每年返台省親,「電腦」二字才會在報上出現一到三次,報紙總會「很驕傲地」寫一筆,說他正在美國研究「電腦音樂」。直到一九六九年秋,我在美國南依利諾大學當研究生,選修「傳播研究方法」才有緣一睹電腦的廬山真面目,並「一親芳澤」,它的「體積」、「相貌」、「速度」與「安放」都不是現在電腦使用者所能想像。看到電腦半世紀來的變化,我想到了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創辦人兼執行總監尼格羅龐悌教授(Nicholas Negroponte),他曾經說過,新科技得經歷三十年才能在社會普及。我第一次見到視像電話是在芝加哥科技博物館,那是一九七一年,但要等到二千年左右我才看到有人使用可傳收視像的手機,而如今幾乎已人手一機了。手機之前的新科技得算電視,它的發展和普及不也類似嗎?看來,尼格羅龐悌的「三十年法則」還頂「靈」呢!時代和科技變了,但人們所關心和擔心的事變了嗎?
黃懿慧教授的講題是〈網路、危機溝通與理論挑戰〉,她從陳冠希「淫照事件」的危機溝通講起,談到中國大陸郭美美事件引起的中國紅十字總會信任危機的溝通,又談到了大陸客來香港狂掃奶粉事件。網路改變了信息流傳的方式與速度,也增加了政府與企業危機溝通的難度,而中國的案例更在學理上挑戰了源自西方的危機溝通理論。網路與危機溝通不是我的專長,但我同樣關心傳播媒介對社會與個人的影響,這些年來又非常留意西方傳媒裏的中國形象,因此對演講的主題深感興趣。黃老師的研究紮實,條理清晰,演講也很精采,對我啟發良多,所以我專心地聽,也用心地思考。
就危機溝通言,中國大陸企業面對的固然是無地、無時不在的網路,西方國家的企業不也同樣面臨網路的挑戰嗎?那為甚麼他們所遇到的問題沒這麼嚴峻呢?問題的核心不就是人們對中國大陸的企業和他們的產品、甚至對政府都沒信心嗎?在國際上,中國不也愈來愈重視形象和傳播嗎?但為甚麼中國的投資很多,海外形象的改善卻不多呢?這不也是信心問題嗎?我看,只要中國依舊控制傳媒、打壓網路傳播,要求傳媒「和黨中央一致」、做「正面報導」,報喜不報憂,甚至「悲事喜報」,把傳媒對大企業的批評當做「唯恐天下不亂」或「反黨、反中央」,動不動就把西方的批評說成「外國反華陰謀」,指責「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那無論中國在國際傳播上多麼賣力或投資再多,形象恐怕都不會有太多的根本改變。與三十年前比,中國大陸的政經都進步了許多,但當局也該與時俱進,改革、再改革,當前的許多問題也將會容易解決得多。今天,無論在任何社會,沒有傳播一定成不了事,但單靠傳播而沒有事實做基礎也是不成的!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砸」了很多錢,也投注了許多心血,用來改善她在阿拉伯國家的形象,但有用嗎?在我看,沒能起作用的原因和中國的情況是一樣的。
三十年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剛在中國舉步不久,市場經濟也才走穩,「姓社姓資」之爭時有所聞,三十年後,「資社之爭」雖未全然銷聲匿跡,但已鮮有傳媒提及,中國走出了貧窮,不少人更先「富」起來了。三十年前,中國正在經濟政策上「摸著石頭過河」,人們在談中國該往哪裡去。三十年後,懷疑市場經濟的人已鳳毛麟角,但「公平分配」的問題依舊困惱着共產黨和人民,不少人還在談中國該往哪裡去,但已從經濟轉到了政治領域,人們在問,中國也會在政治體制上「摸著石頭過河」嗎?
三十年前,中國與香港都有些「幽微」,三十年後的中國與香港何嘗不「幽微」呢?三十年前,中國還很貧窮,香港也為中國將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而人心浮動,三十年後,中國不再貧窮,香港也更富裕,但中國不變的政治體制照樣叫人擔驚受怕,有辦法的大陸和香港人依然要設法出走、移民。中國的根本問題變了嗎?大陸和香港兩地的「幽微」變了嗎?三十年後,我從香港回到了台灣,今年二月我也終於自政大的教職退休了,一晃,我又在台灣生活了七年。隔着台灣海峽和太平洋,我看著中國的種種大大小小問題,看著香港欲直選特首遭中國大陸打壓而不得,看著中國大陸要在香港強推「愛國其名、愛共黨其實」的「國民教育」,看著、看著,我禁不住要問,今天中國與香港的「幽微」比三十年前減少了嗎?台灣的政治制度已根本轉型,民主、民生與言論自由都比三十年前進步了許許多多,但兩岸關係不明朗,這幾年又飽受全球金融風暴之苦,最近更籠罩在核能是否安全的陰影下,台灣居民也禁不住在問:我們的今天是不是和現在的香港與大陸一樣「幽微」呢?將來會不會變得「更幽微」呢?
我出生在湖北建始,抗戰勝利後在漢口讀幼稚園和小學,因為避「秦亂」,一九五零年才離開中國大陸,經香港到了台灣。在台灣,我從小學、中學、大學而研究所,度過了匱乏、艱困卻安定的二十年。離開台灣赴美留學,我才二十六歲,加入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與新聞與傳播學系服務時,我才三十二歲。十六年後,一九九一年,和許許多多對中共失去信心的港人一樣,我們一家南徙澳洲,我在布里斯本的昆士蘭大學新聞系任教,內子則在中文系「掛單」教華語,三個孩子也都先後進了昆士蘭大學。在布里斯本市,我還和鄺振權一家及好幾名昔日新傳系的學生不期而遇。這一年,昆士蘭大學開始鋪設光纖,網路架好後,我和中大的老友又連結上了,而且還用電郵連絡在香港、美國和台灣的學者投稿,為國際傳播學會的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編了一期「中國傳媒改革」特刊。在澳洲三年半後,我終究耐不住對香江人文與地理的思念,揮別了昆士蘭大學典麗的聖露西亞(St. Lucia)校園,在一九九五年元月一日「回流」香港,一晃,又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任職了十二年,也讓我對香江多了一個懷念的地方。二零零三年春,政大傳播學院的羅文輝教授第二度在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座,他應邀到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講〈傳播的第三人效果〉,閒談時問我未來有何計畫,我想到育我成我的父母已經年邁,便表示已決定退休回台,好就近侍奉父母。羅教授後來出任政大傳播學院院長,他向我要了份履歷。二零零六年九月,我加入了政大傳播學院新成立的「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程」和新聞系。再一年,羅教授卸任院長,二零零九年秋,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把他給「挖」走了。
二零零六年秋,我依依不捨地告別住了將近三十年的香江,回到我度過童年和青春的台灣。但就在這年的五月中,爸爸卻等不及我回來,先走了。和爸爸共同生活了快一甲子的媽媽一下子老了許多,她固然喜歡內子和我帶她出遊,但幾乎沒有一次記得去過哪些地方或做了甚麼事。她的失智症變得嚴重了,對着識或不識的人,總用幾乎相同的話重複同樣的事,她最愛說:「到台灣的時候,他才讀小學二年級,現在他的小孩都結婚了」。這個「他」就是「我」,而「我」已從童年步入了老年。二零零七年九月,爸爸走後一年五個月,媽媽突然病倒,在醫院躺了三個星期,安詳地走了。師範學校畢業的爸爸原本在老家湖北宜昌擔任小學校長,媽媽是同校的老師,武漢大會戰後,日軍又攻陷了宜昌,爸爸投筆從戎,媽媽也隨爸爸的軍旅遷到了湖北西部的鄉下。爸爸和媽媽走了,他們真正地息勞、息憂了,永遠不必再為國事和家事操心了。
我在中國大陸出生,在台灣長大,在香港工作,對兩岸三地都有深厚的情感。看到她們好,我會開心,看到她們壞,我會揪心,甚至憤怒,常常忍不住要「罵」上好幾句。在台灣,我在國立師範大學英文系取得學士學位,在台北建國中學教了一年書,又在屏東空軍幼年學校當預備軍官,服完一年兵役,我就考進了當時全台唯一的新聞研究所,在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我摸索到了學業與事業的方向,也找到了人生的伴侶。轉眼,四十一年過去了,當年的少妻已成了老伴,我們倆都希望能再攜手走個二、三十年。
今年二月一日,在台北木柵指南山麓的政大,我畫下了教書生涯的休止符,但要我的心離開政大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其實,我的心也沒離開過香港中文大學。當年,我在中大新聞系任教,內子則在語言中心教國語,兩人還當過新亞書院志文樓學生宿舍的舍監,用半生不熟的粵語和住宿生溝通。孩子們也在中大美麗的校園長大,一家人都受到中大的薰陶,我看著中大在馬料水幾乎由無到有,我也看着新聞與傳播學院日益茁壯。我們忘不了在新亞書院的日子,忘不了吐露港夜晚的點點漁火,更忘不了新亞書院圓形廣場的民歌比賽,一家大小樂當新聞傳播系的啦啦隊,為新傳系獲得冠軍而開心。在台灣這些年,我每回到香港,總要抽空造訪中文大學,去感染一下中大的人文氣息,緬懷新亞書院創辦人錢賓四教授天人合一的哲學,拿「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校訓自勉。當然,我也會去人文館找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老友,請他們帶我到樂群館的雲起軒去吃麵、聊天、會友。在雲起軒,我多半會首選第二桌,就算已經有人坐在第二桌,我也會禁不住望一眼,懷想博學睿智的勞思光、多聞識食的逯耀東、妙語如珠的魏大公和慎言敏思的劉述先。如今,勞、逯、魏三位「亦友亦師」的昔日同事皆已仙遊,獨餘劉公在台北既述且作。中大的新建築已差不多擠滿了校園,花樹更加茂密,而人事更已經不知幾番新了。
再過兩年,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前身新聞學系將創建八十週年,而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也將慶祝成立五十週年。非常慶幸,因工作之便,我受過這兩間優秀學府的薰陶,見證他們發展成為新聞與傳播教育和研究的重鎮,也看到兩院師生的交流和互訪日多。對學術機構言,八十與五十都是「壯盛」之年,年已八七的政大與年屆五十的中大肯定還會繼續發展下去,我肯定會變得更老,但我對台灣與香港、對政大和中大的情誼與美好記憶則肯定不會變!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五日定稿,台北淡水河畔瞥未居)
*作者由1975年至1991年在中大工作,離職前為新聞與傳播學系高級講師兼系主任,2013年2月從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退休。
這天中午,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黃懿慧教授要在政大傳播學院的「傳播沙龍」上分享研究心得。黃教授是位教學與研究兼優的年輕「老」友,曾在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告系任教,五年半前,中大把她「挖」走了。說來真巧,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九一年,我曾在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前身「新聞與傳播學系」服務十六年之久,如今,兩人對調,她去了中大,我則回到了政大,我的母校。
三十年前,我距不惑之年還差一小截,孩子們常常在中大校園和同事的孩子跑來跑去,並且一起參加在邵逸夫堂舉辦的「兒童才藝表演」。三十年後,「今不稀的七十」已熱情地向我招手,當年猶是小孩的子女也都成家並且有了小孩,老大雖然仍在中大跑上跑下,但身分已從「眷屬」變成了「教職員」,由校園「跑」進了辦公室。三十年前的「四月八日」,我在吐露港旁的人文館與新傳系姚霞及張結鳳指導她們的學士論文,三十年後的「三月二十一日」,我則在台北木柵景美溪旁的政大研究大樓討論論文,進進出出的有新聞系的博士生熊培伶、東亞研究所的碩士生莊欣怡和亞太研究所的捷克碩士生Jan Meissler。三十年前,我在中大指導學生,那是我的職責,三十年後,我自政大「退而未休」,指導學生成了我的樂趣。三十年前的那篇文章是用手寫的,三十年後的這篇文章則是用電腦打出來的。時代變了,科技變了,有沒有沒變的東西呢?
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我忘了去聽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教授的公開演講:〈中國文化演進的幾個階程〉,也沒記得去聽社會系鄺振權老師在新亞書院雙週會講〈微型電腦對社會的影響〉。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初,個人電腦方才面市不久,我要到一九八六年下旬才買了一台386型的桌上電腦,當時這已是新科技,運算功能也頗強大,但從今天的標準看,速度奇慢,記憶體更微不足道。那時擁有個人電腦的人不多,用的是5 x 5的軟碟,以及後來出現的3 x 3硬碟。三十年後,電腦的能量、普及度與影響恐怕是三十年前無法想像的,手提電腦、手機、平板(iPad)電腦早已進入尋常百姓家,記憶體更不知要大過當時多少倍,20G或40G,甚至60G都已不稀罕,儲存量小得可憐的軟碟、硬碟早成了歷史名詞和博物館的收藏品,取而代之的是16G、32G或64G的隨身碟,行動硬碟的記憶卡容量更可高達1T或2T。三十年前,桌上電腦應屬令人稱羨的「時髦」玩意,如今則問津者日稀,有興趣的用家似乎大多是專業人士,完全被超輕薄的平板、筆記本電腦或手機取而代之的日子看來也已為時不遠。
聽說,新傳學院的老友正在替香港規劃一個新聞傳播博物館,這實在是個留住傳播科技記憶的好主意。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我仍在台灣讀大學,只曉得電腦是新科技,那時旅美數學家林二博士每年返台省親,「電腦」二字才會在報上出現一到三次,報紙總會「很驕傲地」寫一筆,說他正在美國研究「電腦音樂」。直到一九六九年秋,我在美國南依利諾大學當研究生,選修「傳播研究方法」才有緣一睹電腦的廬山真面目,並「一親芳澤」,它的「體積」、「相貌」、「速度」與「安放」都不是現在電腦使用者所能想像。看到電腦半世紀來的變化,我想到了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創辦人兼執行總監尼格羅龐悌教授(Nicholas Negroponte),他曾經說過,新科技得經歷三十年才能在社會普及。我第一次見到視像電話是在芝加哥科技博物館,那是一九七一年,但要等到二千年左右我才看到有人使用可傳收視像的手機,而如今幾乎已人手一機了。手機之前的新科技得算電視,它的發展和普及不也類似嗎?看來,尼格羅龐悌的「三十年法則」還頂「靈」呢!時代和科技變了,但人們所關心和擔心的事變了嗎?
黃懿慧教授的講題是〈網路、危機溝通與理論挑戰〉,她從陳冠希「淫照事件」的危機溝通講起,談到中國大陸郭美美事件引起的中國紅十字總會信任危機的溝通,又談到了大陸客來香港狂掃奶粉事件。網路改變了信息流傳的方式與速度,也增加了政府與企業危機溝通的難度,而中國的案例更在學理上挑戰了源自西方的危機溝通理論。網路與危機溝通不是我的專長,但我同樣關心傳播媒介對社會與個人的影響,這些年來又非常留意西方傳媒裏的中國形象,因此對演講的主題深感興趣。黃老師的研究紮實,條理清晰,演講也很精采,對我啟發良多,所以我專心地聽,也用心地思考。
就危機溝通言,中國大陸企業面對的固然是無地、無時不在的網路,西方國家的企業不也同樣面臨網路的挑戰嗎?那為甚麼他們所遇到的問題沒這麼嚴峻呢?問題的核心不就是人們對中國大陸的企業和他們的產品、甚至對政府都沒信心嗎?在國際上,中國不也愈來愈重視形象和傳播嗎?但為甚麼中國的投資很多,海外形象的改善卻不多呢?這不也是信心問題嗎?我看,只要中國依舊控制傳媒、打壓網路傳播,要求傳媒「和黨中央一致」、做「正面報導」,報喜不報憂,甚至「悲事喜報」,把傳媒對大企業的批評當做「唯恐天下不亂」或「反黨、反中央」,動不動就把西方的批評說成「外國反華陰謀」,指責「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那無論中國在國際傳播上多麼賣力或投資再多,形象恐怕都不會有太多的根本改變。與三十年前比,中國大陸的政經都進步了許多,但當局也該與時俱進,改革、再改革,當前的許多問題也將會容易解決得多。今天,無論在任何社會,沒有傳播一定成不了事,但單靠傳播而沒有事實做基礎也是不成的!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砸」了很多錢,也投注了許多心血,用來改善她在阿拉伯國家的形象,但有用嗎?在我看,沒能起作用的原因和中國的情況是一樣的。
三十年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剛在中國舉步不久,市場經濟也才走穩,「姓社姓資」之爭時有所聞,三十年後,「資社之爭」雖未全然銷聲匿跡,但已鮮有傳媒提及,中國走出了貧窮,不少人更先「富」起來了。三十年前,中國正在經濟政策上「摸著石頭過河」,人們在談中國該往哪裡去。三十年後,懷疑市場經濟的人已鳳毛麟角,但「公平分配」的問題依舊困惱着共產黨和人民,不少人還在談中國該往哪裡去,但已從經濟轉到了政治領域,人們在問,中國也會在政治體制上「摸著石頭過河」嗎?
三十年前,中國與香港都有些「幽微」,三十年後的中國與香港何嘗不「幽微」呢?三十年前,中國還很貧窮,香港也為中國將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而人心浮動,三十年後,中國不再貧窮,香港也更富裕,但中國不變的政治體制照樣叫人擔驚受怕,有辦法的大陸和香港人依然要設法出走、移民。中國的根本問題變了嗎?大陸和香港兩地的「幽微」變了嗎?三十年後,我從香港回到了台灣,今年二月我也終於自政大的教職退休了,一晃,我又在台灣生活了七年。隔着台灣海峽和太平洋,我看著中國的種種大大小小問題,看著香港欲直選特首遭中國大陸打壓而不得,看著中國大陸要在香港強推「愛國其名、愛共黨其實」的「國民教育」,看著、看著,我禁不住要問,今天中國與香港的「幽微」比三十年前減少了嗎?台灣的政治制度已根本轉型,民主、民生與言論自由都比三十年前進步了許許多多,但兩岸關係不明朗,這幾年又飽受全球金融風暴之苦,最近更籠罩在核能是否安全的陰影下,台灣居民也禁不住在問:我們的今天是不是和現在的香港與大陸一樣「幽微」呢?將來會不會變得「更幽微」呢?
我出生在湖北建始,抗戰勝利後在漢口讀幼稚園和小學,因為避「秦亂」,一九五零年才離開中國大陸,經香港到了台灣。在台灣,我從小學、中學、大學而研究所,度過了匱乏、艱困卻安定的二十年。離開台灣赴美留學,我才二十六歲,加入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與新聞與傳播學系服務時,我才三十二歲。十六年後,一九九一年,和許許多多對中共失去信心的港人一樣,我們一家南徙澳洲,我在布里斯本的昆士蘭大學新聞系任教,內子則在中文系「掛單」教華語,三個孩子也都先後進了昆士蘭大學。在布里斯本市,我還和鄺振權一家及好幾名昔日新傳系的學生不期而遇。這一年,昆士蘭大學開始鋪設光纖,網路架好後,我和中大的老友又連結上了,而且還用電郵連絡在香港、美國和台灣的學者投稿,為國際傳播學會的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編了一期「中國傳媒改革」特刊。在澳洲三年半後,我終究耐不住對香江人文與地理的思念,揮別了昆士蘭大學典麗的聖露西亞(St. Lucia)校園,在一九九五年元月一日「回流」香港,一晃,又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任職了十二年,也讓我對香江多了一個懷念的地方。二零零三年春,政大傳播學院的羅文輝教授第二度在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座,他應邀到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講〈傳播的第三人效果〉,閒談時問我未來有何計畫,我想到育我成我的父母已經年邁,便表示已決定退休回台,好就近侍奉父母。羅教授後來出任政大傳播學院院長,他向我要了份履歷。二零零六年九月,我加入了政大傳播學院新成立的「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程」和新聞系。再一年,羅教授卸任院長,二零零九年秋,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把他給「挖」走了。
二零零六年秋,我依依不捨地告別住了將近三十年的香江,回到我度過童年和青春的台灣。但就在這年的五月中,爸爸卻等不及我回來,先走了。和爸爸共同生活了快一甲子的媽媽一下子老了許多,她固然喜歡內子和我帶她出遊,但幾乎沒有一次記得去過哪些地方或做了甚麼事。她的失智症變得嚴重了,對着識或不識的人,總用幾乎相同的話重複同樣的事,她最愛說:「到台灣的時候,他才讀小學二年級,現在他的小孩都結婚了」。這個「他」就是「我」,而「我」已從童年步入了老年。二零零七年九月,爸爸走後一年五個月,媽媽突然病倒,在醫院躺了三個星期,安詳地走了。師範學校畢業的爸爸原本在老家湖北宜昌擔任小學校長,媽媽是同校的老師,武漢大會戰後,日軍又攻陷了宜昌,爸爸投筆從戎,媽媽也隨爸爸的軍旅遷到了湖北西部的鄉下。爸爸和媽媽走了,他們真正地息勞、息憂了,永遠不必再為國事和家事操心了。
我在中國大陸出生,在台灣長大,在香港工作,對兩岸三地都有深厚的情感。看到她們好,我會開心,看到她們壞,我會揪心,甚至憤怒,常常忍不住要「罵」上好幾句。在台灣,我在國立師範大學英文系取得學士學位,在台北建國中學教了一年書,又在屏東空軍幼年學校當預備軍官,服完一年兵役,我就考進了當時全台唯一的新聞研究所,在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我摸索到了學業與事業的方向,也找到了人生的伴侶。轉眼,四十一年過去了,當年的少妻已成了老伴,我們倆都希望能再攜手走個二、三十年。
今年二月一日,在台北木柵指南山麓的政大,我畫下了教書生涯的休止符,但要我的心離開政大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其實,我的心也沒離開過香港中文大學。當年,我在中大新聞系任教,內子則在語言中心教國語,兩人還當過新亞書院志文樓學生宿舍的舍監,用半生不熟的粵語和住宿生溝通。孩子們也在中大美麗的校園長大,一家人都受到中大的薰陶,我看著中大在馬料水幾乎由無到有,我也看着新聞與傳播學院日益茁壯。我們忘不了在新亞書院的日子,忘不了吐露港夜晚的點點漁火,更忘不了新亞書院圓形廣場的民歌比賽,一家大小樂當新聞傳播系的啦啦隊,為新傳系獲得冠軍而開心。在台灣這些年,我每回到香港,總要抽空造訪中文大學,去感染一下中大的人文氣息,緬懷新亞書院創辦人錢賓四教授天人合一的哲學,拿「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校訓自勉。當然,我也會去人文館找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老友,請他們帶我到樂群館的雲起軒去吃麵、聊天、會友。在雲起軒,我多半會首選第二桌,就算已經有人坐在第二桌,我也會禁不住望一眼,懷想博學睿智的勞思光、多聞識食的逯耀東、妙語如珠的魏大公和慎言敏思的劉述先。如今,勞、逯、魏三位「亦友亦師」的昔日同事皆已仙遊,獨餘劉公在台北既述且作。中大的新建築已差不多擠滿了校園,花樹更加茂密,而人事更已經不知幾番新了。
再過兩年,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前身新聞學系將創建八十週年,而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也將慶祝成立五十週年。非常慶幸,因工作之便,我受過這兩間優秀學府的薰陶,見證他們發展成為新聞與傳播教育和研究的重鎮,也看到兩院師生的交流和互訪日多。對學術機構言,八十與五十都是「壯盛」之年,年已八七的政大與年屆五十的中大肯定還會繼續發展下去,我肯定會變得更老,但我對台灣與香港、對政大和中大的情誼與美好記憶則肯定不會變!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五日定稿,台北淡水河畔瞥未居)
*作者由1975年至1991年在中大工作,離職前為新聞與傳播學系高級講師兼系主任,2013年2月從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退休。
〈時代和科技變了,問題與感情沒變!〉 前新聞與傳播學系教師 朱立
![〈時代和科技變了,問題與感情沒變!〉 前新聞與傳播學系教師 朱立]()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4月 20, 2013
Rating:
Reviewed by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
on
4月 20, 2013
Ra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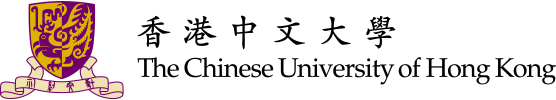








沒有留言: